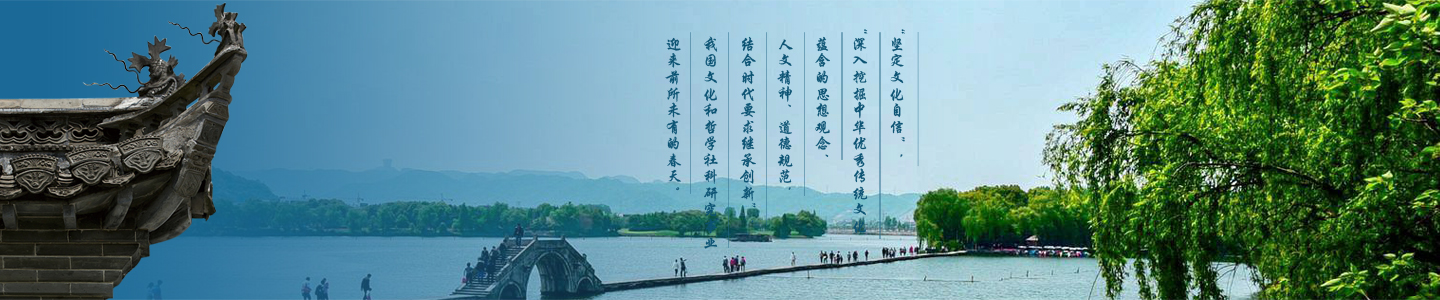我国史籍最早记录越人活动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1世纪末):“于越来宾”。必须说明的是,《今本竹书》为宋人所搜辑,学术价值不能与《古本》相比。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首《自序》说:“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及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所以我们对此书要作一点分内。因为“于越来宾”这一条,恰恰就在“百分之一”以内。按《今本》所载关及越事者共18条,亦惟此条不见于其他古籍记载。特别重要的是,《论衡·超奇篇》说:“白雉贡于越”。《异虚篇》说得更清楚:“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王充撰《论衡》之时,《竹书》尚深埋于汲冢之中,他无疑是根据当时越地传说写此“献雉”之事的。周公于成王七年归政,但由于其声名甚高,越地传说仍称周公,并不矛盾。所以今本《竹书》的这一条可以视作信史,其时距良渚文化的下限不过一千年。
按照先秦人物的年代排列,管仲是最早提及这个地区的人:“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管子·水地》第三九)。几句话,把当时越地的自然环境和越人的低劣素质和盘托出。我们宛如看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一幅图画:在一片潮汐出没、沮洳泥泞的沼泽地上,一批断发文身、又脏又赢的蛮子,在那里挣扎生活。
以后是墨翟,他在世稍晚于越五句践,所以听到一些句践练兵的残暴传说:“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知其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能胜数也”(《墨子·兼爱下》)。越人好勇,这是普遍流行于“中国”的南蛮故事,类似的记载不少,甚至现今还有人认为“越”字从“,是一把砍杀的刀斧,以证明这个民族称“越”的渊源,其说虽谬,但也不必厚非。还有一位庄周,他是公元前4世纪人,当时越国已经败亡,南北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当然较前趋于发达,所以他举了做生意的例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逍遥游》)说明到战国中期,这个地区确实还很落后。最后还可以举《吕氏春秋》的例子。吕不韦虽然入仕于秦,但是生活于战国后期,也算得上是个先秦人物,而《吕氏春秋》记叙之事,多半也是他听到的早年传说,此书《遇合》篇说:“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悦。”这无非是一种比喻,说明“中国”人和南蛮之间的文化差距。《吕氏春秋·知他篇》中记及吴、越二国的话:“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这是先秦“中国”人提及南蛮语言并且指出吴越同语的惟一文献。至于南方人操的是什么语言?《孟子·滕文公上》有一句话概括:“南蛮鴂舌之人”。用现代意思表达是:与“中国”人相比,这些人说的是像鸟叫一样的外语。讨论越文化研究,我写这一段发端,主要是为了说明,在先秦时代,“中国”是“中国”,“南蛮”是“南蛮”,汉人是汉人,越人是越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类,界限是截然分明的。但由于汉人在文化上显然大大超越当时的“四夷”,势力强大,所以不仅可以稳坐自居其“中”的位置,而且提出诸如“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中庸》)之类的绥靖口号,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高,有文字,才有可能为“四夷”的先秦史和先秦文化积累宝贵的资料,于越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研究古代越史和越文化,从文献资料上说,大多要依靠先秦的汉人著作。例如“于越”这个名称以及越人第一次到“中国”朝聘——这是于越从传说时期进入历史时期的标志。
此后,事情逐渐起了变化,南蛮人开始强大起来。首先是与于越“习俗同,语言通”的句吴,他是南蛮中最早崛起的一族。但从现存的文献记载看,它与“中国”的沟通比于越要晚得多,一直要到吴王寿梦元年(前585)才“朝周适楚”(《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但《左传·宣公八年》已记及吴,故“寿梦元年,朝周适楚”以前当有漏记)。却随即向“中国”动武,《左传·成公七年》(前584):“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后来又发生了这“一族两国”多次战争,最后是《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越王句践于是挥军北上,迁都琅琊,称雄“中国”。这一番过程,在先秦的汉人文献《春秋经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如我在《论句践与夫差》(原载《浙江学刊》1987年第4期,收入于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一文中所说,越国是在战国七雄之前最早称雄的国家。它囊括了从今山东东翼直到今钱塘江以南越故地的大片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必然都有较大发展,可惜我们很难从文献资料中检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先秦的“中国”文献中,只记及它的武功,如《墨子·非攻下》:“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而《吕氏春秋·顺民篇》记及齐庄子以攻越之事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但“猛虎”并不持久,《古本竹书》魏武侯十七年(前380),即越王翳三十三年:“于粤子翳迁于吴。”由于王族内部篡杀相继,如我在拙著《于越历史概论》(原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所述,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越王无疆(或作#伐楚大败,为楚人所杀。《越世家》说楚“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国的世系从此断绝,但浙江(钱塘江)以南的故越地仍为越所有,《越世家》说:“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按《古本竹书》魏襄王七年(前312):“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派公师隅北上的这位越王是谁?史籍没有记载,当时距无疆败亡不过20多年,这位不在越世系记载之中的越王就能以这样一大批物资远送“中国”,说明于越的世系虽绝,但还有较大的潜在力量。
前面讨论的越史与越文化,都是根据先秦的“中国”文献,对于于越来说,这些文献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由远离越地的汉人按当时流行的传说写成的文字,对于越史特别是越文化,后世的研究者不免有一种瞭望和鸟瞰的感觉。因为从这些文献中,人们看到的于越,还仅仅是一个并不清晰的轮廓。所幸于越自己还留下了一宗重要的文化遗产,即越地越人的先秦文献《越绝书》。此外还有少量在东汉之初身居越地的学者们的著作,成为后人研究越文化的重要源泉。
对于《越绝书》,我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接触,虽然饶有兴趣,但一直感到从文字到内容都有许多不解之处。以后随着年龄增加阅读面的扩展,才对此书逐渐有所理解。从20世纪40年代起陆续做点笔记,探索一些问题,如作者、卷篇、版本、佚文等等方面。到50年代开始撰写论文,却因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和最后的“十年浩劫”而搁置。70年代末期,因学校学报索稿才发表了这篇《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的论文。由于《四库提要》循明人之说,以此书卷末几句隐语定其作者为东汉袁康、吴平,后人多深信不疑,所以我撰此文加以驳正,其实我所提出的观点前人也已议及,我只是作了一些解释,认为此书应为先秦著作,但东汉初人对此书作了整理补充。
此文甚得学报的重视,为了刊物卷首的英文目录,他们特请当时外语系主任鲍屡平教授与我商量翻译之事。鲍先生精于英语,但疏于这类冷僻的古籍。由于文中提及清李慈铭对此书之名的解释(《越缦堂日记》三函十二册,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他很认真地去查了《越缦堂日记》。而我实在并不赞同李氏的意见,所以最后他还是按我的理解,把书名英译作TheLostHistoryofYue。在当时,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译法,所以并不介意。但以后几次去日本讲学,却有好几位日本学者与我谈及,说他们原来对此书书名颇有不觧,看了这个英译,才使他们豁然开朗。让我很感谢鲍先生的处事认真。所以后来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我又重提了此事。
前面说到《四库提要》因循明人而把作者定为东汉初人,对此我是很早就不苟同的。上述此书书名的英译就表达了我长期来的见解。东汉去春秋已远,虽然于越传说如“献雉”之类在越地流传的还有不少,但若无一样底本或其他成帙的素材,怎能写出如此一部大书来?特别是像《吴地传》和《地传》两篇,单凭传说是绝对拼凑不出来的。此书之所以称“绝”,必然是于越世断绝以后,越人虑越史之绝而撰写的。所以写作年代必在无疆败亡,越人返回浙东故越地以后。当时,越人中的上层人物受汉文化熏陶已深,汉字在越人中流行已久,所以越人已能捉笔作书。而从书中记吴地、越地甚详,而未及句践北迁后定都200余年的琅琊,说明作者是无疆败后从吴返越人物,并不熟悉琅琊之事。
《史记·孙吴列传正义》引《七录》,称《越绝书》有16卷,隋唐《三志》著录同。但从宋代起已经缺佚,今本作15卷,共19篇,与宋以前的本子相比,缺佚已逾十分之二。但与前述先秦“中国”人的几种文献相比,其内容显然要丰富得多。此书《吴地传》和《地传》两篇,记载今苏州和绍兴一带的山川地理、风土民俗甚详,因而被称为是地方志的鼻祖(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此书有多篇记叙句践与夫差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以至最终灭吴等史事,因而被认为是“复仇之书”。(小万卷楼本《越绝书》清钱培名《跋》)。此书记及军事、战略、兵器的篇幅不少,所以有人认为是“兵家之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七)。此书又记及许多农田水利,畜牧养殖,旱涝灾异,并涉及各种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所以也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陈桥驿《越绝书序》,袁康、吴平《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越绝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与前述各种先秦“中国”人所撰的文献相比,许多资料都是此书所独有,所以值得珍贵。可以随手举个例子,前已提及,越人没有文字,而古代越语也早已消亡。先秦汉人提及南蛮语言的唯有《孟子》的“鴂舌”。但此书中却保留了不少古代越语。如我在《绍兴方言序》(杨葳、杨乃浚《绍兴方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中指出的:“除了含句、乌、朱、姑等属于人名和地名的专门名词外,还记及了‘越人谓船为须虑’,‘越人谓盐曰余’,‘夷,海也’,‘莱,野也’,‘单者,堵也’等几个普通名词。”所有这些,我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已叙其详,这里不再赘述。东汉初人袁康、吴平整理此书,是此书得以流传后世的一个重要机遇,是功不可没的。而他们在整理工作中,还增加了当时流传的于越故事和补充了先秦以后的资料。所以他们的工作,属于早期的越文化研究。从袁、吴的工作联系到东汉初期,这实在是越人流散以后越文化研究的发端时期,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从现存的成果来看,除了《越绝书》以外,还有《吴越春秋》和《论衡》两种。从保存越文化资料的价值来看,《越绝书》当然是首要的。但《吴越春秋》和《论衡》的价值,也都远远超过先秦的“中国”人著作。所以对于这几种文献,今天的越文化研究者,必须加以特别的重视和仔细的钻研。所以有必要把《吴越春秋》和《论衡》这两种早期的越文化研究成果也略作说明。前者是山阴人赵晔的著作,其体例属于编年史,内容除当时越地流行尚多的先秦故事以外,主要还是参考了《越绝书》,所以清钱培名《越绝书札记》(《小万卷楼丛书》,又附于张宗祥点校《越绝书》卷末,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说:“赵晔《吴越春秋》,往往依傍《越绝》。”不过从体例说,《越绝书》是以事立篇,各篇并无明显联系。而此书是一部按年代编撰的于越(包括句吴)的完整史书,有裨于后人研究先秦越文化的系统概念。此外,赵晔时代的《越绝书》当然还是完整的足本,今本《吴越春秋》中有不少《越绝书》所不载的资料,除了赵晔自己的搜集以外,必然还有今本《越绝书》的佚文,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在此书中获致许多他书所无的独家资料的原因之一。还要指出的是,今本《吴越春秋》也并非东汉完书。《四库提要》说:“是书前有旧序,称隋唐《经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十卷,殆非全书。”这话不错,现在我们可以从其他古籍中检录的此书佚文不少,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资料。如《水经·渐江水注》:“《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于越曾立都诸暨北界的埤中,这是越史和越文化中的大事,都为今本所佚,并为其他任何古籍所未曾记及。至于万历《绍兴府志·序志》说它“杂以谶纬怪诞之说”,这话也不错,但是应该考虑到,赵晔撰书之时,上述先秦“中国”人所撰诸书(包括《越世家》)他都能看到,所以此书中的“怪诞之说”有许多是属于“外转内”的,现在把这些文献进行对勘,大部分都能查实。由于我往年曾撰有《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原载《杭州大学报》1984年第1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对此书有较详评论,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说《论衡》,此书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并非专叙越地越事,而且今本也有较多缺佚,我往年曾撰有《论衡与吴越史地》(原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1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作过说明。虽然今本论及的越中故事不多,但由于王充是一位博学多才、见识超群的学者,所以《论衡》中记及的越地越事,实在不同凡响。书中也记入了一些当里越地流行的传说,但是经过他的判断筛选,所以没有收入那些被先秦“中国”人(包括《越世家》)检去的荒谬不经的东西。像“象耕鸟耘”这类在上述这些文献中都有记载的荒唐故事,只有他出来作了科学的解释。特别是对于有些至今还有人捧牢不放的如“越为禹后”和禹到会稽召开全国诸侯大会等荒谬绝伦的故事,也都由他出头一笔否定。例如《书虚篇》的“禹到会稽,非其实也”;“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夏禹巡狩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在《恢国篇》中,他干脆否定了先秦时期(例如《尚书·禹贡》)所谓的“大一统”:“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王充,他不愧是一位科学地研究越文化的前驱。
东汉以后的漫长年代里,越文化的研究没有多少成果。由于先秦“中国”人的著作流行一时,而后来的《史记》《汉书》等在一个尊经崇儒的社会里具有极高的威望,致使越为禹后、吴为周后等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既没有出现像王充这样的人物,也无人继承和发展《论衡》的成果。
当然,局部的研究还是有的,而且也得到一定的收获。例如对于于越语音的研究,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吴地“号曰句吴”:“句音钩,夷族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四“于越”云:“《春秋·定公四年》,书于越入吴。注云,于,发声也,《史记》又书为于越,注云,发声也。”这实在是在《越绝书》的基础上,对“鴂舌”语音的又一次发明,是对后人越语研究的重要启发。清李慈铭所谓“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清李慈铭《息茶日记》,载《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或许就是受唐宋人启发的成果。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秦一统以后越人流散的研究。其中首先是胡三省在《通鉴》汉纪四十八“山越”下所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这才让人明白《后汉书·灵帝纪》记及的“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此“山越”原来是秦驱逐越人时就地逃入深山的。另外,明焦竑:“此即所谓东越、南越、闽越地。东越——名东瓯,今温州;南越始皇所灭,今广州;闽越即今福州,皆句践之裔。”(《焦氏笔乘续集》卷三)。这对秦一统以后越人流散与分布的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东汉以后的漫长时期中,可以称道的越文化研究,或许就是上述几例而已。
越文化的跃进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见识宽广,根底扎实,治学勤奋的史学家,他们既深入钻研古代有关越人的大量文献,又细致地鉴别分析这些文献,先后提出了不少前无古人的科学创见。如顾颉刚、罗香林、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诸氏,都发表过在这个课题中不同于前人见解的论文。其中特别是顾颉刚。我在《大禹研究·序》(《大禹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序又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中。一开头就指出:我生平十分佩服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在相关科学还比较落后,利用相关科学的成果和资料都比较困难,却能依靠自己的优厚天赋和非凡勤奋,依靠自己的观测、实验、思考,提出当时让人大吃一惊而事后逐渐获得证实的假设、学说、理论的科学家。因为我是一个地理学者,在这门科学领域中,这样的科学家有两位。
我在此《序》中提出的第一位是创立“大陆漂移说”的德国科学家魏根纳(AlfredLotharWegener1880-1930)。《序》中接着说:“在魏根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的十余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顾颉刚(1893-1980)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论点:‘禹是南方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会稽(越)’。”顾颉刚提出这种大胆假设的年代,正是蔡元培创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学术界确实呈现出一番活跃气象,但是把这位传统的第一个朝代的开国之群置于南蛮鴂舌之人的神话之列,在当时显然是许多人都容不了的。如我在《大禹研究·序》中所说:那时候础颉刚还是一个年轻人,竟敢提这样一个与中国的儒学传统挑战的离经叛道的学说。当时,地质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学和考古学等相关科学,在理论上和检测手段上都还相当落后,他是依靠自己的笃学、慎思、明辨等功夫提出来的。此文一出,一些人佩服他的胆识,另一些人即欲鸣镝而攻。在顾氏提出这种假设以后十年,另一位思想开放的学者冀朝鼎,用英文在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AllenandUnwinLTD)出版了一本《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的论著,此书第四章以《禹和洪水的传说》为题,对顾氏的观点作了议论。虽然在那个时代,他还无法判断这种观点的是非,但是对于这种大胆的假设,他给予极高评价。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越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第一是研究者的队伍空前扩大,若干高等院校也加入了这种研究的行列,并且还建立了几处越文化研究所,有稳定的研究人员。
第二是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为了交流和讨论这些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曾经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
第三,这或许是这段时期越文化研究获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前面提及的相关科学的进步,在研究队伍中,除了以往的历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民族学者和部分考古学者以外,地质学、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者等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而原来的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必须依靠先进的旁支科学的研究成果。此外,由于科学的测年手段的出现和应用,过去从文献里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往往可以迎刃而解。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批越文化研究者在去年进行了关于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的实勘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越文化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值得学术界特别是越文化研究者重视的。按照近年来的研究,古代越人的流散开始于史前,我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文化交流》第22辑,1996年)一文中指出,卷转虫海时期出现了越人的第一次流散,他们的足迹遍及台湾、越南、南洋群岛、日本甚至太平洋。
秦一统以后,越人又出现了第二次流散,除了遁入深山的“山越”以外,他们的流散地区遍及浙西、皖南、赣、湘、闽、两广、海南、云贵等地。通过对古代越人流散地区的实勘调查,必然可以获得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的实迹,这实在是越文化研究中的一条独特和重要的蹊径。
回顾以往,越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展望示来,我们充满信心。
1陈桥驿.我对清史编纂的管见[J].学术界,2003,(3).
[2]Ernest J.Eitel.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eing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M].Tokyo:Sanshusha,1904.
[3]Klein’s Comprehensiv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Amsterdam: Elsevier PublishingCo.,1971.
[4]戴 望.管子校正[A].诸子集成[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5]孙诒让.墨子闲诂[A].诸子集成[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6]王先谦.庄子集解[A].诸子集成[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7]邹逸麟.谭其骧论地名学[J].地名知识,1982,(2).
[8]陈桥驿.越绝书序[A].袁 康,吴 平.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陈桥驿.绍兴方言序[A].杨 葳,杨乃浚.绍兴方言[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10]顾颉刚.古史辨[M].北平:朴社,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