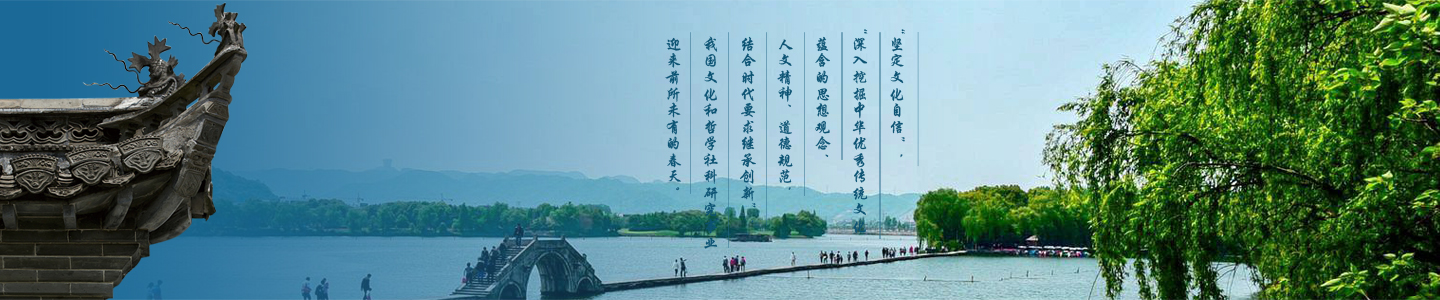潘承玉
众所周知,台湾与祖国大陆地理上一水相连,形同母子;两岸人民唇齿相依,交往频繁,情若兄弟;台湾文化沐浴中华文化的雨露成长,并因而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整体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均速发展的,而是在近四百年来才由早期的若即若离忽然获得加速发展的;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整体其他部分的关系也并不是均衡的,而是有突出重点的,换句话说,中华文化整体中其他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对推进台湾与中华文化整体关系发展的贡献并不是均等的。比如,论者曾经大量地谈到台湾文化与闽文化的紧密关系,这使“闽台文化”一词早已成为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本文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华文化整体组成部分之一的越文化与台湾的关系亦十分紧密,撇开先秦时代越族先民与台湾高山族的古文化渊源不论,仅以近四百年来出自越文化核心地区的三哲沈光文、姚启圣、鲁迅而论,他们就对近世以来台湾与中华文化母体关系愈益紧密的加速进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该进程发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一、沈光文:中华文化在台湾系统传播的开创者
“台湾自来被视为海外仙山、海中孤岛,为土番游息田猎之场,绝少汉人足迹,虽自隋、唐以迄宋、元,典籍偶亦书及斯民斯地,然而大规模的开荒拓土,应数明末郑成功的大量来台。”[1] 实际上,在郑成功之前,来自越文化核心区域的沈光文已经筚路蓝缕地在台湾传播了中华文化十年。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他在台南民众中享有持久不衰的庙祀和被两岸古今学者广泛称誉为“海东文献初祖”就是一个突出证明。但历史价值的存在正依赖于人们的不断重温。
沈光文是在颠沛流离、坚忍不拔的抗清斗争中,因为意外的原因到达台湾的。他字文开,号斯庵,浙东宁波府鄞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 1612 ),乃陆象山门人沈焕后裔、万历中首辅沈一贯族孙,明末著名哲学家、杰出爱国学者刘宗周、黄道周弟子。崇祯三年( 1630 ),参加浙江乡试,中副榜;崇祯九年以明经贡太学。弘光元年( 1645 )南都覆亡,光文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建立监国政权,以太常博士衔参与组织“画江”之役。次年绍兴被清军攻陷,光文又追随鲁王转战厦门、金门各地,并居间联络郑成功等抗清志士;又深入广东肇庆,参与永历政权抗清行动,被授予太仆寺少卿。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 1651 ),光文从潮州航海至金门,值清福建总督方招徕明朝遗臣,“ 密遣使以书币招之”,他愤而“焚其书,返其币” ,“时粤事不可支,公遂留闽,思卜居于泉之海口,挈家浮舟过围头洋口,飓风大作,舟人失维,漂泊至台湾”[2] 。当明北都覆亡,清人顺便雀占鸠巢,开始其严重的民族压迫统治时,沈光文刚刚三十三岁,正是求取功名的大好时光,但他没有选择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道路,而是任凭一腔爱国热忱的驱使,投身到反抗民族压迫的艰难斗争中。此后,他被迫远离抗清斗争的前方,但他的爱国追求没有停止,只是转换形式罢了。
从至台湾,到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去世,沈光文在台湾生活了三十七年,这三十七年同样是欢愉极少、艰辛时长的,但它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却是非同寻常的。第一阶段:因有亲戚先期到台湾并和荷兰人关系密切,沈光文先被已统治台湾二十八年的荷人头目尊为宾师,充当与明郑势力的联络人;后荷人发现郑成功有攻台计划和他的立场所在,光文遂被监视住居,备历险危困苦而泰然处之 。仍暗中绘制台湾地形图以为郑成功攻台预作准备,不慎露出端倪,被荷人看出,父子一起遭到逮捕囚禁、严刑拷打。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荷人毫无所获,才把他们释放。从入台开始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这十年,是沈光文在荷兰人统治下传播——当然是暗中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阶段。其时,岛上基本没有文化可言;有之,也是荷兰人因与土著人打交道而扩散的荷语、荷文和基督教信仰。第二阶段:郑成功和他的不少文臣武将都是沈光文的朋友,所以收复台湾后他们和他的团聚曾给沈光文带来短暂的快乐。但为时不到一年,“已而成功卒,子经嗣,颇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军亦日削。公作赋有所讽,乃为爱憎所白,几至不测。公变服为浮屠,逃入台之北鄙,结茅于罗汉门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于经,得免。山旁有曰 [目]加溜湾者,番社也,公于其间教授生徒,不足则济以医,叹曰:‘吾廿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经卒,诸郑复礼之如故”[3] 。由此可见,沈光文的托迹台湾,还是希望把这里作为真正的抗清基地,从而有朝一日从清人手里收复故土,重会故乡,但他对明郑第二代嗣王郑经有背抗清事业倒行逆施的直言批评,使他过早丧失了参与政治事业的资格,被迫过上二十年左右沉沦民间的生活。这是他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阶段。其时的明郑政权是以大明政权的合法继承者——南明永历朝廷的残疆自居,以推翻“满夷”统治、恢复汉族主体的中华衣冠文物制度为号召的,因此,沈光文本人虽形同流放,但他的教授生徒、传播中华文化的事业,却是至少不为当权者所反对的。以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十八岁就中乡试副榜的文化素养,以二十年间被剥夺参与政治从而拥有的常人所没有的时间、精力,加上一种对故国的神圣使命感,自然使他的传播中华文化事业取得了台岛第一人的成就。第三阶段:光文生命的最后五年,也是清领台湾的最初五年。其主要事迹,一是拒绝清福建总督、浙东同乡姚启圣的招请;二是集清吏与硕果仅存的遗老结唱“东吟社”:“时耆宿已少,而寓公渐集,乃与宛陵韩文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衮、郑延桂、榕城林奕丹、吴蕖轮、山阳宗城、螺阳王际慧结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4]
沈光文三十七年的流寓生涯到底给台湾留下了什么?作为学者专家公认的“第一个为台湾带来中华文化的大陆文人”[5] ,“中国文化在台湾的第一个播种者”[6] ,“台湾文化的启明导师”[7] ,他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贡献最主要的到底有哪些? 浙东史学大家全祖望考察沈光文一生事迹,在其《沈太仆传》的最后写道:
公居台三十馀年,及见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后,海东文献,推为初祖。所著《花木杂记》、《台湾赋》、《东海赋》、《檨赋》、《桐花赋》、《芳草赋》、古今体诗,今之志台湾者,皆取资焉。呜呼!在公自以为不幸,不得早死,复见沧海之为桑田,而予则以为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盖天将留之以启穷徼之文明,故为强藩悍帅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终依依故国,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岂无述作,委弃于毡毳,亦未尝不深后人之痛惜。公之岿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见于世,为台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渊之恨矣。[8]
由此可见,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个贡献在于,由于享寿年高和著作侥幸未被焚毁,沈光文给台湾留下了第一批汉文文学著述,其中包括有关台湾地理风物的记述。这些著述成了台湾地方文化发展史上极重要的文献,往后撰述台湾方志者皆要以之作为参考。康熙间台南第一任诸罗知县季麟光对此深加称颂说:“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斯庵来而始有文矣。斯庵学富情深,雄于词赋,浮沉寂寞于蛮烟瘴雨中者三十馀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无巨细皆有记载。其间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僧寮、禽鱼、果木,大者纪胜寻源,小者辨名別类;斯庵 真有心人哉!”[9] 简而言之,沈光文给台湾留下了第一批汉文文献资料,包括第一批有关台湾地方文化的资料。中华文化的载体汉文,是沈光文第一个带到台湾的;属于中华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台湾的汉文著述,是沈光文第一个创造的。此即“海东文献,推为初祖”之由来。
上述记载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沈光文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爱国深情和民族气节带到了台湾,这是他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二个贡献。所谓“ 咸淳人物,盖天将留之以启穷徼之文明” , 是大有深意的。“ 咸淳”为南宋末度宗的年号,“咸淳人物”本指由宋入元而拒绝出仕蒙古族政权的汉族遗民,借用作具有坚定民族气节,绝不出仕满清朝廷的明遗民的代称。在另一个地方,全祖望将沈光文与 抗清志行坚确的另两个同时乡贤钱肃乐和陈士京相提并论:“吾乡残明遗臣葬于闽中者三:钱忠介(肃乐)公在古田,尚称内地;陈光禄(士京)在鼓浪屿,则濒海矣;沈太仆在诸罗,则海外矣。……夫三公之勋业有大小,其名亦有显晦,然其依恋故国则一也。”[10] “虞渊”为神话中日落之地,“虞渊之恨”亦即大明灭亡,不能振兴之意。近代史家追溯其时沈光文以文学创作发抒其故国沦亡之恸、以明其坚定民族气节的影响曰;“台湾三百年间,以文学鸣海上者,代不数睹。郑氏之时,太僕寺卿始以诗鸣。一时避乱之士,眷怀故国,凭吊河山,抒写唱酬,语多激楚,君子伤焉!”[11] 沈光文的“为台人破荒”,他之被后人深深追思,决不仅是留下一堆普通的汉文文献,而是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播种在了台湾。
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三个贡献,在于深入原住民之中,设帐授徒,间悬壶行医,数十年实际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系统地将中华文化播洒到台湾最底层的民间。顺治十八年( 1661 )、康熙三年( 1664 )先后随郑成功、郑经来台的大陆人士不乏贤才。但他们大多只是活动在固定的寓公文化圈子里,而与广大的台湾原住民无甚接触;即使偶有接触也为时甚短,如来自松江府华亭县的徐孚远曾在新港一带的山地开垦,但郑成功卒后即携子离开,回返华亭老家(半途病卒潮州)。郑经经营台湾期间采纳陈永华 “ 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三十年之后,足与中原(清朝)抗衡”建议,创立孔圣文庙,并“命各社建立学校命,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始于康熙五年,时间既比沈光文晚,又因这种教育体制,是由小学而州试,“州试有名者移府,府试有名者移院,各试策论,取进者入太学”,“三年大试,拔其尤者补六科內都事”[12] ,具有招徕性质,而不象沈光文那样是走向底层原住民,长期与他们打成一片;具有应试、应仕教育的性质,因而教育的内容受到限制,不象沈光文那样从传统的儒家六经到实用医学都可以教授、传播。由此可见,沈光文是第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台湾底层原住民社会者,对台湾社会逐渐摆脱荷兰统治期间的文化印痕,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中获得发展影响深远。
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第四个贡献,也是最直接的贡献,在于他以“雄于词赋”的杰出才艺“成为‘台湾文学'的始祖”[13] ,为蛮荒的台湾带来中国文学的曙光和芳香。他的创作是中国古典文学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成长、壮大的第一棵树,后来台湾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其主导样式、主要文学活动形式、主要精神取向无不与他相关。沈光文擅长辞赋而尤工诗,不仅将“春秋亡而后诗作”的儒家精神贯注到自己的作品中,还继承明末文人结社以文学创作寄托忧国之思的传统,创建了台湾第一个诗社,此后台湾文学的发展形成以诗为主的特色,诗人每当重大历史变动之际辄好联社唱酬、砥砺名节,可以说都奠基于沈光文。就沈光文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来说,除歌吟台湾风物之作外,主要的就是明其抗清不渝的民族气节,如《隩草》云,“义旗嗟越绝,剩得此顽民”,“一自椎秦后,同人在海山。冠裳不可毁,节义敢轻删”;或述其穷困饥饿的潦倒苦节,如《柬曾则通借米》云,“迩来乞食竟无处,饥即驱我亦不去;甑中生臣兴索然,餐风吸露望青天”,“苦节尤难在后头,一日不死中心忧”[14] 。然而更多更感人的还是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有家不得归的无奈糅合在一起的抒写乡愁之作。如《葛衣吟》“故国山河远,他乡幽恨重”,《望月》“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方”,《怀乡》“万里程何远,萦回思不穷”,《思归六首》之一“待看塞雁南飞至,问讯还应过越东”,之三“家乡昔日太平事,晚稻香新紫蟹肥”,之六“故国霜华浑不见,海秋已过十年淹”[15] 等。文学史家称道沈光文的诗“开创了台湾乡愁文学的先河”[16] ;但其实,那不仅是单纯的对越东故土的乡愁,也不仅是他个人的乡愁。
那是这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对其文化母亲的乡愁,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渐脱离蛮荒的台湾对中华文化母体的依恋。
二、姚启圣:台湾与中华文化母体首次完整团聚的设计者
因为拒绝同乡一开始带有政治性质的招抚,沈光文的归乡梦终被耽误,他的乡愁和他的生命一道消融在宝岛的泥土之中[17] ;但在文化上获得初生的这座岛屿对中华文化母体的依恋,却凭借他这位杰出同乡的远见卓识和智慧而获得一次空前的舒解。这位同乡就是从越文化核心之地、越国故里走出的姚启圣。他是中国历史上台湾与中华文化母体首次正式团聚的设计者,从此,中华文化才真正全方位的登陆台湾。
姚启圣,字 熙止(又字熙之),号忧庵,浙江 绍兴府会稽县人。生于明天启四年( 1624 ),少任侠多智,为诸生。明南北两都相继覆亡,绍兴南明鲁王监国政权亦一载而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回,遂放弃无谓抗争,出游四方。至扬州府通州,受侮于当地某土豪,于是以干才得权知州事,假职杀之而归。又以道途手刃两劫掠民女的八旗满兵,亡命北上,入籍镶红旗汉军。康熙二年八旗科举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岁比不登,前令坐负课系狱者七人;公叹曰:‘明年增吾为八矣!'乃张乐置酒,出七人于狱,痛饮之,为治装遣归”,“时澳门贼(海盗)霍侣成披猖獗,督、抚不能制,公以计擒之”[18] 。康熙四年四月未经朝廷旨意,擅自“招抚海寇黄起德等四千馀人”,被广东总督疏报朝廷,“下部察叙”[19] 。康熙六年又以擅开海禁被罢官[20] ,“识者多悲其不遇,而公之志浩然不衰”[21] 。
姚启圣的擅开海禁之举在清初汉人官吏中绝无仅无,和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再次先开海禁以及在台湾回归中原政权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都直接相关。清廷出于对沿海抗清武装实施坚壁清野政策,防止其军事渗透,特别是割断他们与沿海百姓联系的需要,早在顺治十二年六月就下令,“严禁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22] 。顺治十七年又先在福建施行迁界,顺治十八年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更全面厉行迁界禁海政策。这无疑是对几千万沿海人民世代安居生息权利的剥夺。以广东来说,康熙元年二月,“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次年再迁,结果,“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馀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误出墙外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23] 。先后七任知县皆因无法完成清廷的国课征收而下狱,沿海民生的凋敝达到何等程度不难想见。姚启圣擅开海禁,并带头下海,用船装运中国的传统贸易品瓷器去和住在澳门的欧洲商人交易,无疑是对困敝已极的民生危机的疏解,是他后来再次大规模开禁的一个预演。他力主收复台湾的动机也可以从这里找到。
罢官以后,姚启圣发挥他善于经商的才能,短短七年间积累了数以十万两银子计的巨额财富。[24] 但三藩之乱的烽烟一起,他就带着家人和全部资财投身到浙闽沿线,凭借平定叛乱的军功一路高升,康熙十三年署诸暨知县,十五年擢福建布政使,十七年晋福建总督,十九年又以挥师攻克金门、厦门再晋兵部尚书,创造了平步青云的典范。这是他个人的成功,也是对国家从三藩之乱中迅速恢复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他一生最大的骄傲,他对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贡献还不在此,而在在清朝收复台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这一历史过程知之不详的一般人,只把清朝对台湾的收复归功于两个人:康熙皇帝和施烺,前者是决策者,后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直接指挥者。实际上,这二人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姚启圣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他是亘立在他们二人之后、之间的一个人物,是清朝收复台湾重大举措的提倡者、策划准备者和两位主要军事统帅之一,是台湾与中华文化母体首次正式团聚的设计师。
全祖望《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劈首就这样写道: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闽督姚公用密计授水师提督施烺下台湾,七日破之,诏封烺为靖海侯,而公自陈无功,故赏亦不及。是年十有一月,公疽发背薨,归葬于越。
呜呼!蒍子冯为楚画平舒之策,及其身后,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蒍子之功也”,归封邑于其子。羊叔画平吴之策于晋,及其身后杜预、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羊太傅之功也”,告之于其庙。古人旂常之公论,如此其覈也;唐裴晋公之平淮,则李凉公不免有惭德矣。然凉公之有憾于碑,非敢以掩晋公也,特欲轩之颜允、古通之上耳,且所争亦不过在文字,而酬庸之典,则自晋公而下,颜允、古通固无不及也。今公以航海数千里之提封,滨海数百城之巨患,三世不宾之馀孽,累年筹运,一旦而廓清之,又并非蒍、羊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移之别将,溘然长逝,并不蒙秬鬯黄肠之泽,虽在劳臣报国岂敢有言,而彼偃然开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25]
这位史学大师的不平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覈实公论。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三藩之乱逐渐平息后,他在福建总督任上为解民倒悬,千方百计劝退八旗驻军、开解海禁和谋划收复台湾等一系列举措:
初……迁界之议起……而闽益贫。及精忠至,封山圈地,莫敢裁量,且日益耗。已而耿、郑之乱交作,杀掠所至,不知谁兵。闽中驻一王、一贝子、一公、一伯,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所将皆禁旅。无所得居,则以民屋居之;无所得器械,则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无所得役,则即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系其老幼,喑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横至,日有死者;加以饥谨,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闽,蒿目伤心,谋所以拯疲民者,无所不用其极。……公言于(康亲)王曰:“今陆地已无贼,材官蹶张,必不能秣马而驱之波浪之间,则所重在舟楫,不在韅靷鞅靽也。而军需乏匱,禁旅所养且三万,一马日费谷斗有六升,计一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马一食足养水师三十万人,非但为民,实为国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奏愾告闲乎?”……公连上三疏,……天子乃允公,诏王班师。……而禁旅将驱男妇二万馀人去,公流涕力请于王,令军中敢有私携良民者杀无赦,而公则赎之以金,临发尽取以还民。……于是始请开界……自撤兵,而闽人出汤火之阨;更开界,而闽人得耕鱼衣食之资,相与狂号喜跃曰:“姚公活我!”
公乃大造八桨船、 舟良 船、双篷船,并请招红夷夹板船以图台湾……[26]
《台湾府志》本传载其在此之前,已经“自备衣粮,招募壮勇,有澄清海外之志。尝曰:‘国家声教无外,今逆藩虽已削平,而以台湾一弹丸廑宵旰忧,使沿海居民不遑宁处,罪将谁归?'会总督郎廷相罢去,以启圣代之。于是得为所欲为,而平台之计决矣。”[27] 可见结束对峙,造福两岸民生,实现国家在文化教育上的大统一,在文武双全的姚启圣早有打算,是思之已熟、筹之已久。然而,有些思想保守的朝廷大员看不到在三藩之乱后收复台湾的必要性和及时性,竟然将此看作他的一大罪状。如康熙二十年四月,就在姚启圣全面着手收复台湾的将领挑选、军事部署和后勤准备时,远在北京的左都御史徐元文在一份 奏本中 别有用心地 攻击他:“ 海坛进师,启圣力为阻挠;一则曰不敢轻举丧师辱过,一则曰不敢以封疆为儿戏。及恢复海坛,继取金门、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其始则养寇,其继又欲穷兵。……启圣有卒数万,与海坛万馀之贼相持三载,不能成功,乃欲令水师提督统新降之众远涉波涛,以图万一之侥幸。”这位前方将帅收复台湾的远大战略连同他相机进退的具体举措,一起遭到无端的指责和贬低。在受命回复的奏折中,姚启圣对此据实予以驳斥,其中明白写到:“臣先于十八年九月有密陈‘一统规模'清字(按即满文)一疏云:‘前得厦门弃而不守,亦不再攻台湾,将船只尽毁,以致海贼复起,我兵无船可用;今托皇上洪福,如得厦门之后即进剿台湾,不难破卵覆巢。'是臣欲攻台湾,始终如一,非既得厦门,方请宜取台湾也。”[28] 包括大量其他史料清楚地记载[29] ,康熙帝在和明郑集团前后断续和谈十多年之后终于决策在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乃是姚启圣反复上疏陈请并告之事机的结果;康熙帝在较长时间失去对施烺的信任后对其又大加重用,也是姚启圣以全家性命竭力保举的结果;姚启圣本人还是这场军事行动的总指挥、预先准备者、后勤保障者和前线两指挥之一。他在跨海作战的指挥舰上写下的诗篇是何等的豪迈而又不乏文人的浪漫多情:“提师渡海极沧溟,万里波涛枕上听。此际梦回香阁里,千峰明月一孤舲。”[30] 虽然收复台湾的首功和他擦肩而过[31] ,虽然迄今也只有极少数学者认识到“姚启圣是清廷统一台湾的核心人物”[32] ,但历史自在,公论自在。袁枚为其所作传结尾载:“初,厦门有石文云:‘生女灭鸡,十亿相倚';人多不解。及台湾平,或曰:‘十亿',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酋'旁,鸡也;灭鸡,灭郑也。”[33] 民间的口碑堪称最好的历史。
姚启圣的促成台湾归于中原大一统政权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某种程度上比郑成功的收复台湾还要重要。全祖望在考察这件大事的历史意义时曾说,“台湾自生民以来,不通上国”[34] 。如果我们把“通于上国”看作中原大一统政权直接在台湾建署设官,行政理民,那么,全祖望所言姚启圣之前的台湾,的确是历史的事实。郑成功及其后裔在台湾的统治,实际上只是个割据的分裂的地方政权。台湾之归于清朝版图,是台湾成为中原大一统政权有效管理组成部分的第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其时中国历史已经完成明清易代的转变,清朝政权也完成了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加速的汉化过程,从关外“野蛮”的“异族”政权转变为一个相当“正常”的中原大一统政权:其以儒家传统为经国方略,已和汉唐明各代无甚区别。无论是从“中原所在,则正统所在”的地理正统观还是从“礼义所在,则正统所在”的道统正统观来看[35] ,到三藩之乱前后,清朝都已成为中国的正统所在,成为中华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和当代象征。曾经抗节不仕的明遗民纷纷放弃当初的立场,或馀生入宦如朱彝尊、陈维崧,或精神加盟如黄宗羲、万斯同,或交往清廷大吏如屈大均、顾炎武,其子弟后代能出仕清廷者更无不勉力为之,吴三桂的起兵造反亦极少被看作值得欢呼的复明大业,皆反映了清廷正统地位的被接受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和人心所向。在民族矛盾已经不再成为最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时代,明郑势力以反抗民族压迫为借口继续存在,使两岸人民继续“不遑宁处”,这种分裂、对峙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姚启圣帮助历史适时地结束了这一局面,也帮助台湾和中华文化母体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团聚。在大一统政权的机制之内,中华文化的雨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全面、深入、持久地泽及宝岛的各个角落;宝岛自身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通过参与中华文化整体的运行进程而焕发出迷人的风采。
三、鲁迅:现代中华文化对台湾挣脱日治回归母体的呼唤者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总如人们所愿。大清王朝的庞大机器在开动二百六十七年后颓然停止运转,变成一堆废铁,彻底丧失了中国正统与中华文化当代象征的地位。由于腐败无能,在其灭亡前十六年即光绪二十一年( 1895 )的春末,清朝甩手把台湾割让给日本,造成了台湾与中华文化母体的新的分离。
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又诞生一大批巨子,他们为改变中国积贫即弱、老大衰卖、任人欺凌的现状而在各个方面战斗、流血流汗的同时,也对台湾摆脱日治回归中华文化母体,发出直接或间接、有声或无声的呼唤。从越国故里走出的鲁迅,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2004 年初,一篇题为《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的通讯,见诸香港报章:
“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日前浸会大学举办的“鲁迅节座谈会”上表示,是鲁迅令他从小就认定中国内地是自己的祖国。
陈映真是在鲁迅去世后的一年,即一九三七年出生。父亲热爱中国文学,他从父亲书房的隐蔽处发现了鲁迅的《吶喊》,从此便爱不释手,这本书更成为了他思想的启蒙。
他说:“鲁迅作品虽描写中国的落后与黑暗,但全是出自他的关怀和热爱,使我从小就认识到中国内地是自己的祖国,我不会像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嘲笑她的落后、贫穷,虽然鲁迅作品中有很多的讽刺,但比讽刺多好几百倍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和爱护。因此,我从小就笃定这国家是我的,我要爱护她。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他影响着一个隔着海峡、隔着政治,偷偷地阅读他著作的一个人。”[36]
这已不是陈映真第一次这样表示。如果说陈映真的话代表了与其同龄的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心声的话,那么,比他更早出生的一代人、两代人,他的父兄之辈和同龄人中间,有这种心声的人一定更多,他们思想中朦胧存在或清醒意识到的这个感觉也一定更为强烈。因为不论是从陈映真的年龄,还是从其追忆“从父亲书房的隐蔽处”的细节来看,陈映真开始读鲁迅作品的时间都应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知道,那是鲁迅著作在“光复”后的台湾被当作“反动文人”之什遭到国民党政府严禁的时代;再往前推到陈映真出生的那一年,又恰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为配合侵华战争的发动采取限制中文书籍流通政策,造成鲁迅著作实际上第一次被禁的开始。鲁迅的著作即使在连续被禁的年代,即使对一个没有什么理性知识的童稚少年,也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心灵冲击,那么,不难想象,在那之前,它们的影响该是何等的广泛;在更多台湾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知识阶层的心灵中,鲁迅该拥有何等崇高的地位;在台湾人民抵制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皇民化”改造,重新找回祖国的感觉,从而促成战后台湾顺利回归中华文化母体的过程中,鲁迅和他的著作又成为何等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
不错,由于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几近八年,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生涯都萌生和开始于日本,同时,受到恩师藤野先生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的深刻影响,鲁迅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持久的“日本情结”,如拥有许多在华日本朋友,与日本文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翻译了为数不菲的日文作品,常常从对比的角度抨击古老中国的文化劣根性而对日本民族流露出明显的好感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宣称:“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37] 他断言日本民族善于在模仿中创造、革新,“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而中国则有“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38] 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鲁迅在世当年就被有些人扣上了“亲日派”的帽子。但是,一方面,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鲁迅观照日本只及其长不及其短,完全是出于中华民族“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以达到自我扬善抑恶的目的[39] ;另一方面,鲁迅并没有把日本民族、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他对日本民族、日本人民的明显好感并没有妨碍他在根本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严厉批判。例如,他谴责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40] ,愤怒地指出,“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41] 。他质问国民党政府镇压爱国学生抗日请愿的“友邦惊诧”论,“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42] 他把胡适的答记者问,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痛斥为是替日本征服中国出谋划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出卖灵魂的秘诀”[43] 。等等。正因为鲁迅能够如此将日本民族、日本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清晰地区别开来,既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经,也谴责其他帝国主义的帮凶行为,同时心中又有一个“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44] 的愿景;既能够如此无情地揭露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各种病痛,同时又提出“中国的脊梁”依旧存在,“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45] ,鲁迅才既非为个人经历而丧失民族立场的媚日派,又与狭隘民族主义者不可同日而语;既非自甘落后的民族自大狂,又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判然有别;总之,才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而为全体国人包括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所深深景仰,他和他的作品才作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优秀代表,成为连接和维系台湾和中华文化母体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这种纽带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两个互相联系的途径,一是鲁迅与代表台湾社会“未来”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交往,二是鲁迅创作对代表台湾社会“灵魂”的台湾现代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这位“民族魂”很早就有一颗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在满清王朝统治下的民族耻辱感是他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个伤痕。“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46]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47] ,他曾不止一次这样道出早年的感受。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尊心和耻辱感,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才成为鲁迅虽未数数然宣之于口却耿耿然横亘于怀的一个隐痛,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痛苦遭遇才在他心里引发一种难以名状却清晰存在的感同身受。如鲁迅在 1927 年为一个台湾青年的译著作序时所自道: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 [军]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 “ 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 ” 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48]
鲁迅没有在文章中经常直接提台湾,当出于这种“暂且放下”的原因。然而,“暂且放下”,又哪里能真的放下得了;台湾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耻辱经常还是不经意地闯入他的笔下。例如,在此之前不久,他回答一位柯某人的“卖国”攻击,就愤然写到,“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49] ;他在厦门停留期间,写信告诉友人,不为良辰美景所动,“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50] ;等等。因为这种与异族统治下台湾同胞心灵的息息相通,鲁迅才在上面的序文后接着写道:“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鲁迅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青年的“困苦”确实感同身受;而让后者更为感动的,还是鲁迅对他们既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的爱国之举的充分肯定和鼓励。鲁迅从平凡的台湾青年身上看到了他们可贵的爱国热肠,也看到了台湾和其中华文化母体的未来;台湾爱国青年则把鲁迅看作自己的精神知己和导师,这是鲁迅和台湾青年交往的思想和感情基础。鲁迅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与张我军、张秀哲、张深切、郭德金等台湾青年的交往早有专文考证[51]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没有这一思想感情基础,他们的交往就不可能那样广泛、密切和持久,也不可能凭其足够深远的辐射力成为鲁迅在精神上与台湾社会沟通的一个管道。
当然,鲁迅在现代中华文化史上的基本定位首先还是在文学方面,他是那个时代公认最杰出、最优秀、影响最大的作家,可以说,台湾现代新文学作为祖国大陆现代新文学的一个支流,正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发展的。以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来说:张我军是台湾现代新文学的先驱和最主要的理论倡导者,他是鲁迅的学生。他把类似国内《新青年》的刊物《台湾民报》源源不断地送给鲁迅,听取鲁迅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看法和指导意见,又通过这份最有影响的刊物的转载把鲁迅的小说介绍给台湾读者,他本人的创作也竭力学习和仿效鲁迅,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赖和是台湾现代新文学创作实绩最大、最受人们敬重的作家,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的鲁迅”,他是鲁迅的崇拜者。他继承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抗争色彩和批判锋芒,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反帝反封建尤其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又一战场,并从鲁迅的解剖一般国民劣根性走到对殖民地国民性格的批判和鞭挞,而用心同样在于唤醒沉迷的民众以实现民族自救。台湾新文学的另一个重要作家杨云萍后来也谈到他们那一代文化人所受到的鲁迅的影响;“民国十二三年 (1923 — 1924) 前后,本省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下,也曾掀起一次‘启蒙运动'的巨浪。而对此次运动,直接地,间接地影响最大的,就是鲁迅先生。他的创作如《阿 Q 正传》等,早巳披转载在本省的杂志上,他的各种批评、感想之类,没有一篇不为当时的青年所爱谈,现在我们还记忆着我们那时的兴奋。”[52]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既是中国大陆现代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台湾现代新文学的一个指南;鲁迅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是如此的全面、深刻,从而必将其“民族魂”的思想光芒辐射到台湾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鲁迅,这位从越文化故里走出的文化巨匠,这位现代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优秀代表,这位现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英雄,在台湾还在日据时期,就悄然把他的“民族魂”投射到广大的台湾人民心中,就给了广大的台湾人民而不仅仅是后来的陈映真一个心中的“祖国”。台湾能够在与中华文化母体分离整整五十年后于 1945 年顺利回归,不能说不与这位中国“民族魂”人物的感召相关。难怪杨云萍要在文章中写道:“台湾的光复,我们相信地下的鲁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53]
不幸的是,台湾在与中华文化母体再次团聚不到五年,又重新分离了。虽然由于“国府来台”,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不免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有多少收获可以补偿它与中华文化母体的分离?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三位越地先哲,如果地下有知,将曷胜浩叹!
[1] 黄哲永 : 《清代台湾传统文学作家 ‘童蒙教育'的养成教材》,收入东海大学中文系编《明清时期的台湾传统文学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4页 。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太仆传》,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第499页。
[3] 同上。
[4] 同上,第499-500页。
[5] 杨若萍:《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之历史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2年博士论文(指导教授:皮述民),第9页。
[6] 陈昭瑛:《台湾诗选注》,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版,第11页。
[7] 施懿琳:《从沈光文到赖和——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8] 《沈太仆传》,《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500页。
[9] 季麟光:《题沈斯庵杂记诗》,收入龚宪宗编《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台南县立文化中心,1998年版,第219页。
[10] 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五《从亡诸公之二》卷首,四明文献社,民国七年校勘本。
[11] 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四《艺文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28种,台北大通书局,1962年版,第615页。
[12] 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 128种,第268-269页。
[13] 杨若萍:《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之历史研究》,第 9页。
[14] 全台诗编辑小组(主持:施懿琳):《全台诗》第一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5页、第39页。
[15] 《全台诗》第一册,第51页、第44页、第40页、第59-61页。
[16] 刘登翰等:《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 第 104 页 。这也是台湾学者的广泛共识。如台湾大学陈昭瑛教授《台湾诗选注》沈光文小传(第 11页) 即云,“台湾之乡愁文学亦滥觞于他的诗作”。
[17] 据 《沈太仆传》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499-500页) 载:“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兵下台湾,诸遗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闽督姚启圣招公,辞之。启圣贻书讯曰:‘管宁无恙?'因许遣人送公归鄞,公亦颇有故乡之思,会启圣卒,不果。 ……寻卒于诸罗,葬于县之善化里东堡。 ”
[18]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九《名臣·姚 熙之尚书事略 》,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35页。
[19] 《清圣祖实录选辑》,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 165种 ,台北大通书局, 1963年版,第20页。
[20]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郑氏史料三编》卷一《刑部残题本一》 : “姚启圣照依出界律斩首,事在康熙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赦前免罪,仍行革职,永不叙用。”见《台湾 文献史料丛刊》第175种 ,台北大通书局,1963年版,第76页 。《鮚埼亭集》卷十五《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 误在“时公年五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288页)即康熙十二年,李桓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姚启圣·国史馆本传》 误作 康熙 “ 八年 ,以擅开海禁,罢任”(《台湾 文献史料丛刊》第230种 ,台北大通书局,1967年版,第532页 )。 清末迄今,凡有学者述及姚启圣生平亦均误此事在康熙八年,显缘后者而来。
[21] 钱仪吉:《碑传集》卷十五《康熙朝功臣传下 · 姚少保启圣传》,《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22] 蒋良骥:《东华录》卷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9页。
[2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 迁海》,《屈大均全集》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24]《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姚启圣·国史馆本传》 载康熙二十年五月姚启圣回奏康熙帝语, “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革职后贸易七年,颇积微赀”(《台湾 文献史料丛刊》第230种 ,第535页 )。
[25]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278-279页。
[26]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283-284页。
[27] 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十五《名宦 ·姚启圣 》,《台湾 文献史料丛刊》第74种 ,台北大通书局,1961年版,第417页 。
[28]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姚启圣·国史馆本传》,《台湾 文献史料丛刊》第230种 ,第534-536页。
[29] 除姚启圣本人的六卷《忧畏轩奏硫》、两卷《忧畏轩文告》和魏源《圣武纪略·康熙勘定台湾记》外,还有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卷二《海东纪胜》载:“(郑氏)立郑克塽为主,年幼,政出多门。福建总督姚启圣知之,密请东征,朝廷可其奏。”李元春《台湾志略》卷二《戎略》载:“启圣制闽数载,建议平台,独握胜算,……谈论指授,英气激发,为定谋推轂名臣第一。”施烺《靖海纪事》卷上《飞报大捷疏》云:“督臣姚启圣捐造船只、捐养水兵,与臣共襄大举,仍又亲来厦门弹压,殚心催缵粮饷,挽运不匮,加以厚资犒赏将弁,三军莫不激励思奋。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赏赉鼓舞之功,乃有此成效也。”等等。
[30] 《视师吟》十首之一,《忧庵大司马并夫人合稿·忧畏轩遗稿》,宣统《越中文献辑存》本。
[31] 《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载,台湾收复, “烺乃遣其子弟由海道自津门先告捷而后上露布于公”,且“公之告捷也,使者由驿道行”,遂迟至多日,“乃以首功封烺。将以次及公,公疏言:此庙谟天定,微臣无力”,“未几,有召掌中枢之命,而公已不起”。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286页。
[32] 徐晓望:《论姚启圣为统 —台湾所作的历史贡献》,载《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3期。广泛检索可以发现,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姚启圣的研究仍然极少,有关的论著还不到施烺研究的二十分之一,这是很不应该的。
[33]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姚启圣·传》,《台湾 文献史料丛刊》第230种 ,第540页。
[34] 《会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279页。
[35] 钱钟书对此有相当全面、精辟的考述,见其《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6-1490页。
[36] 载香港《大公报》, 2004年2月23日第2版。
[37] 《“日本研究”之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38] 《〈出了象牙塔之后〉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第243页。
[39] 潘世圣:《鲁迅的日本观——鲁迅体验和理解日本的主要内容及特征》,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40]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13页。
[41] 《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09页。
[42] 《“友邦惊诧”论》,《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59页。
[43] 《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78页。
[44]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13页。
[45]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118页。
[46] 《又是“古已有之”》,《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23页。[47] 《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4页。
[48]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429 页。
[49] 《聊答“……”》,《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42页。[50] 《厦门通信》,《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75页。
[51] 秦贤次: 《鲁迅与台湾青年》,载《鲁迅研究月刊》, 1991年第10期。
[52] 《纪念鲁迅》,载台北《台湾文化》第 1卷第2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1946年11月。
[5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