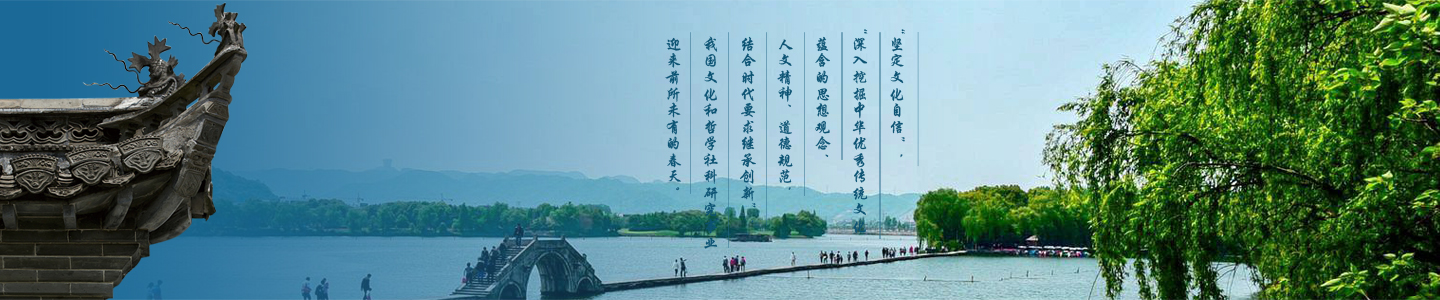越文化源远流长,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均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特别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史书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故绍兴有“名士乡”之誉。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垄断产生知名人物的专利权,任何地方都可能产生某些优秀人物,但像绍兴那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连绵不断地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从而形成令人瞩目的“名士文化”现象,这在别的地方确实是罕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越文化这块土壤中是否具有某种文化“基因”,在历史的嬗变中形成了特殊的文化“血脉”,以至于名人辈出,绵延不绝?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伟大的文化巨匠鲁迅,是绍兴众多杰出名士中的典型代表。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诚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正由于他深受越文化的影响。越文化悠久厚重而又优秀的传统,是最初滋润鲁迅这棵“独立支撑的大树”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鲁迅首先是从区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某种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
综观越地众多名士,明显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一是突出的“精英”特征。绍兴的历代名士,多是在各自领域中作出了杰出贡献,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精英式人物,如东汉的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为中国地方志之鼻祖。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是中国第一部炼丹术专著,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文化大交流,寓居越地的贺循、王羲之、谢安、孙绰、谢灵运、嵇康等,都是名士大家;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兰亭修禊聚会,王羲之撰写的《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宋元,有贺知章、陆游、杨维桢等诗人。陆游为我国古代诗作最多的爱国诗人,有“六十年间诗万首”之说,前人评为“亘古男儿一放翁”。明清,有著名心学大师王阳明,蕺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浙东学派的中坚人物黄宗羲,被吴昌硕称为“画中圣”的青藤画派的创始人徐谓,被后人评为“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之杰出画家陈洪绶,散文大家张岱,提出“六经皆史”的新史体创立者章学诚,“海上画派”的主要创始人任伯年。至近现代,除周氏兄弟外,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著名高能物理学家赵忠尧、钱三强、数学家陈建功、人口学家马寅初等等,都是各相关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其二是讲操守,重气节,轻生死,具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硬气。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或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越人身上往往迸发出刚正不阿,坚贞不屈,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眩目光芒。鲁迅曾说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有这种“硬气”的人物可谓比比皆是,例如魏晋时的嵇康,因“刚肠疾恶”而为司马昭所不容,临刑一曲《广陵散》,成千古绝唱。明会稽沈炼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严斥严嵩父子。终被严嵩罗织罪名处死。明末山阴王思任,怒斥奸相马士英“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宣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拒绝马士英退避绍兴。后清绍兴城破,他紧闭大门,大书“不降”两字,同时的山阴刘宗周,清以礼相聘,刘书不启封,并勺水不进,壮烈殉国。山阴祁彪佳,亦拒绝清之礼聘,置《别庙文》与《绝命词》于桌,自沉于寓园梅花阁水池中。志书记载:“东方渐明,柳陌浅水中,露角巾寸许,端座卒矣,犹怡然有笑容”。至于清末的徐锡麟、秋瑾,世所皆知。还有近代的马寅初,解放前,他抨击时弊,国民党当局用尽种种手段,也无法压制他的声音。解放后,他的《新人口论》,被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煽起全国性的大围剿,但他拒绝检讨:“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其三,在思维特性上,坚持独立性,不盲从,对所谓的正统文化或理论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和反叛意识。在区域文化的关系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明显的文化偏见,即把中原文化周边的众多部族,贬之谓“北狄”、“南蛮”、“西戎”、“东夷”,越为“南蛮”之一,管仲曾说过:“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极而垢”。但越人对自己的文化却富于自信。史书曾记孔子往见越王句践;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践答曰:“失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东,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态度异常坚决地谢绝了孔子:“夫子异则不可”!杨义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引言》中也提到此事,认为“这两种地域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二千年后的鲁迅非孔,原因很多,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地域文化因缘。”(1)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称赞他“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王充著《论衡》,以“实事疾妄”为指导思想,严厉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等虚妄迷信。徐渭自谓“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章学诚生在乾嘉之世,他激烈批评的正是“乾嘉学风”:“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他提出“六经皆史也”,诚如侯外庐所言:“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而马寅初之《新人口论》,则更是大逆“时趋”,然而“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历史终于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以上所述三点,我以为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越地名士文化中的“DNA”,它们在鲁迅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鲁迅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和所取得的成就,世所公认,无人可及。鲁迅《狂人日记》等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鲁迅又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鼻祖,《野草》至今还被认为是散文诗的经典之作。甚至鲁迅文学史学术研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其水平至今也无人能超越而鲁迅之精神气质,一个“硬”字当可概括,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面对黑暗努力,他横眉冷对,决不折腰,不管是“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还是“拉大旗作虎皮”,“化了装从背后给一刀”,或者换掉姓名射来的“暗箭”。至于鲁迅对所谓正统、传统的理论、观念的反叛和批判意识,则更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思维特征。鲁迅在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到自己的“习性”:“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在《我要骗人》一文中又说:“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他曾借“狂人”之中,振聋发聩地喊出:“从来如此,便对么?”从而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满篇“仁义道德”字面背后,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越文化中的这种“基因”,最早形成于越族史前时期漫长的岁月中,构成了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渗透于代代相延的越人血脉之中。此后,同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在这块文化土壤上,一些杰出人物先后涌现,在他们身上集聚了越文化优秀精华,隐性的文化基因得到了显性的张扬,又因此成为后人可以有意识地仿效的楷模,这种良性的循环造成了越地特殊的文化名人链,也可谓之“文脉”。因越地地理历史条件相对稳定,此“文脉”千年流淌,乃形成了特殊的“名士乡”现象。
首先,越族是文明起源最早的中国古部族之一。在绍兴偏西约100公里之建德山地发现的距今约5万年之“建德人”,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之越人最早的祖先。在绍兴偏东近70公里发掘出来的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5000年,被视为越文化之嚆矢。绍兴西边之余杭所发掘的距今约5000年之良渚文化遗址,可能也是越人当年的一个部落聚居中心。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河姆渡文化,鉴于河姆渡文化以及别的一些文化遗址的新发现,以致1999年有100位海内外著名史学教授联名建议,重写中华古史:“过去中华文明一直被误认为单纯的农业文明,起源于西北黄土高原,是一种封闭的大陆文明。其实不然。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浆、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过去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之源,一切重要的发明创造都先产生于北方,然后才向南方传播。试举一例:直到现在有些历史书中仍说养蚕缫丝为黄帝正妃嫘祖发明,但在黄帝之前的两千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已经有丝织工具的图像,足证古书记载失实。近年来,考古发现与民俗调查的许多研究成果说明,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均先兴于南方。我们承认在三代以下,黄河文明已经形成中华文明主流;但是也应该承认,就文明的起源而言,南方更早于北方这一历史事实。”(2)确实,越文化在它的史前时期,就显示了在此后历史时期中一脉相传的敏于发现,善于创造,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英”特征。其次,根据历史地理学、第四纪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从晚更新世以来,在今宁绍平原一带,曾经发生过三次海进和海退。约2.5万年前的第二次海退后,背山面海,水土资源丰富,又属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的宁绍平原上,形成了河姆渡文化。但又发生了第三次海进,距今7000-6000年前达到了最高峰,原来在这片自然环境非常优越之地繁衍生息的越人,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部族迁移,而最后大部分越人随着平原环境的恶化不断向南部山区移动,最终会稽山成为越人聚居的中心。与山会平原相比,会稽山地水土贫瘠,越人不得不在生产上从种植业为主倒退到农猎并举,如《吴越春秋》所记:“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以给食”,其实即是刀耕火种。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为求生存,越先民面对现实,显示了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在洪水的包围之中,越人在会稽山地居住了3000多年,漫长岁月中造就的这种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必然深深地溶入于这一民族的血液之中、意识深处,形成该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集中反映在他们所创造的“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史学家顾颉刚在他的《古史辨》中就推断:“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在越”。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也持同样观点,他在《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一文中提出:“禹的传说就因为卷转虫海侵而在越族中起源,然后传到中原。”在《越族的发展和流散》又说:“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的山麓冲击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祖辈口口相传的,如今已为洪水所吞噬的美好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天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3)神话传说中的“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其实是曲折地反映了越先民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的精神和他们的期盼。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人类还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用具体形象来代替逻辑概念是当时人们思维的特征。例如,他们没有勇猛、精明这一类抽象概念,却通过想象创造出希腊神话中的珂喀琉斯和尤里塞斯这样的英雄来体现,所以他认为神话英雄都是“想象性类概念”,是某一类人物概括起来产生的形象。维柯认为,是人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神话是“真实的叙述”,不过它和诗一样,不能照字面直解,它是古代人类认识事物的特殊方式,是隐喻,是对现实的诗性诠释。当我们透过这种“隐喻”,确实可以发现越族中特别是其代表性人物所形成的“名士文化”中始终存在,此后仍不断显露的那种极硬、极韧、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特征,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如此,在以后的社会斗争中也同样如此。再次,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也决定了越文化在思维方面的批判性特征。越文化的思维特征其基础是崇实。上文已提到,越先民在非常困难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这决定了他们实事求是的基本思维特征,诚如丹纳在谈到古代的日耳曼民族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的尼德兰时说:“为了要生存,要有得住,有得吃,有得穿,要防冷,防潮气,要积聚,要致富,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和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像德国人那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入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行动的号召太普遍了,太急迫了。而且连续不断;一个人只能为了行动而思想。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做遗传。”(4)崇实必反对虚妄迷信,二者相伴相生,故强烈的批判意识必然也是越人的重要文化基因。所以,越文化名人多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杰出的批判家。当然,除了史前时期所造成的“遗传”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一是越地在中原文化圈之外,曾被视为“南蛮”,从而造成文化上的逆反心理,正统的文化濡染相对也少;二是历史上曾有数次南北文化大交汇,思想较开放;三是越位于东海之滨,史前时期即具海洋文明特性,明清以来,又首先承接“西风东渐”,思想不僵化。
越文化中的这种“DNA”,在众多越“名士”身上都或多或少地留有印痕,而鲁迅当为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越人特征颇令人注意。当年他初去日本,在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同学就有评语:“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1926年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陈源以散布“某籍某系”的流言,嘲讽周氏兄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其实也说明他们也注意到了鲁迅与越文化之内在的深系。还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毛泽东曾作七绝二首,其一曰:“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其二曰:“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前一首说的是鲁迅的胆识,后一首却转而赞誉鲁迅的故乡绍兴名士的爱国主义传统,显而易见,毛泽东也甚注意以鲁迅为代表的越地名士身上所一脉相承的越文化印痕。
越地名士身上的越文化影响,既有如荣格所说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遗传”所致,更有后人对本区域文化中优秀传统的有意识的汲取和追求。还以鲁迅为例,他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曾主张:中国的文化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有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在某些特定语境中有时更语出惊人,不无偏激,但也只是“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在整体性的反叛之中,依然还存在着一种寻根意识,以求“取今厚古,别立新宗”,例如鲁迅很赞赏汉唐的闳放和雄大的魄力。但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自宋元以降,“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他确认以儒学为核心,儒道释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正统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关注的“固有之血脉”,其实正包括某些地域文化,我这儿指的主要是越文化。由于多种原因,某些地域文化尚未完全为正统文化所同化而“硬化”,恰恰是在这种地域文化之中,还多少保留有“固有之血脉”的生气、野气和活力。杨义曾把战国时期的越文化概括为“剑文化”,“所谓剑文化,蕴涵着复仇、尚武、砺志自强的精神素质”,杨义敏感地注意到:“也许鲁迅已经隐约地感受到:古越文化是他所见到的国民庸懦心态的解毒良剂。”(4)鲁迅在写于几乎和《文化偏至论》同时的《摩罗诗力说》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死症。孔子是“强以无邪,即非自由。许自由于鞭绊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而“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鲁迅认为这种传统文化造成“天下太平”,终于使屈原这样敢于“放言无惮”的诗人也受到影响,在诗篇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说:“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刚烈,抗拒战斗,渐进于文明矣,化定俗移,转为新懦”。面对中国正统文化的“硬化”,要破不撄之治,重振武健刚烈,“剑文化”不啻是值得继承、发扬之文化精髓。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时间,在故乡他同时开始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作为区域文化的越文化的启蒙教育和影响。鲁迅出生于书香、官宦家庭,幼时的鲁迅比较规范地读完了四书五经。但身为越人,尤其是因家庭变故而感受过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对世俗的、区域的文化更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层的联系。李欧梵曾经提出过“小传统”和“大传统”两个概念:“鲁迅的‘反传统’的倾向与他对通俗故事、寓言、民间宗教仪式、神话社戏等‘小传统’的爱好密切相关。……他的一篇较长的回忆录《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富有诗意地回顾了他的孩提时代的两个世界:以花园象征着浪漫有趣的小传统世界和以私塾先生的书屋为代表的索然无味大传统世界。”(6)李欧梵所谓的“小传统”,显然主要蕴含了区域文化的内涵,而“大传统”则无疑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李欧梵这段话,提示了两种文化传统的并存现象和对立性,以及鲁迅明显的情感倾向。
应该指出,越文化也同样存在着一个鲁迅所说的“硬化”的问题。在现实的层面上,鲁迅对故乡的一切并不赞赏,甚至不无厌恶。当年正因为深感世态炎凉,看透了家族内外“世人的真面目”而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对S城人的憎恶让人震惊:“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但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寻找事实上似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1910年,他不得已又回到故乡,故乡的人事仍然让他厌恶,这清楚地表现在他其时写给许寿裳的一些信中:“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鬼域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越中棘地不可居”,“越中学事,惟从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在小说中,“鲁镇”“未庄”里也未见有什么可以让人首肯的人、事。然而,在历史的层面上,鲁迅对越文化的优秀传统充满了一种自豪之情,仅王思任的一句“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在鲁迅《全集》中就先后提及了五次之多,鲁迅甚至很坦率地表白:“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越文化历史上的优秀传统,才正是鲁迅所要追寻的“固有之血脉”。
历史学中“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认为: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所谓长期的连续性是指“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即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而短期的急剧变化象一阵又一阵冲击着岩石的海浪一样,将长期的连续性冲破了,并且产生了“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这是一场非常壮观的人间戏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杰出人物。”(7)
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以后并未因时间、空间的间距增大而疏淡,恰恰相反,随着视野的开阔,对中、外文化整体了解的深入,而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对越文化精髓的“寻根”,特别是对历史上越地先贤精神的追寻。1909年从日本回国,至1918年在北平绍兴会馆发出《狂人日记》这一声“呐喊”,在这十年中,我们明确地发现他挖掘故乡地域文化精髓的执着的追寻轨迹。从1911年起,鲁迅开始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此书辑录八部有关古会稽郡的史传和地方志佚文,1915年以周作人名义刊行。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说:“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为一集。中经游涉,又闻名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讥于世。俯仰之间,遂辍其业。十年已后,归于会稽。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是故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显然,鲁迅此举,并非是“夸饰乡土”而己。1913年3月,鲁迅辑成6卷本《谢承后汉书》,并作序。此书还在1912年4月间,鲁迅已在南京作过第一次校抄,后在北京又对照不同版本抄录、校订。1913年9月,鲁迅又有意于整理《嵇康集》,23日,他遍寻琉璃厂各书肆,未见一本《嵇康集》,一周后,在京师图书馆借到吴宽丛书堂钞本10本,即抄作底本,自此至1935年,前后校勘《嵇康集》长达23年。
《新生》之夭折,使鲁迅曾有过的“梦”破碎了,他自此进入了“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然而“这经验使我反省”,“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在这一文化追寻的“转向”之中,无疑,“越文化”成了他关注的重点。鲁迅的“呐喊”,并不始于南京初读《天演论》之后,也不在更广泛接触了“新学”之日本时期。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当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后他却陷入了“寂寞”之中;然而,在近十年的沉默之后,在“S会馆”中“回到古代去”的“麻醉法”下,他却爆发了!对1918年《狂人日记》石破天惊的问世,我们难道能无视鲁迅十年沉默期中对越文化的追寻与这一声“呐喊”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研究绍兴的“名士文化”现象,从历史学和区域文化学的角度讲,确实应该注意“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这两个方面。绍兴多名士,而许多名士正出现于急剧变化着的历史转折时期,特别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而鲁迅这位杰出人物,就正出现新、旧世纪之交,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越文化有着“长期的连续性”,这在中国各个区域文化中是非常突出的,它有着特别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这是“名士文化”的基础性条件;而“短期的急剧变化”,是给了“长期的连续性”的文化积淀所积聚的能量,提供了因高速碰撞而释放的契机,诸如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坚贞不屈的品性气质、聪颖过人的天赋等,因历史的碰撞而光彩夺目,正有利于我们从中把握越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1)《杨义文存》第四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3)《吴越文化论丛》第46页,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版。
(5)《杨义文存》第五卷第55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6)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