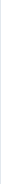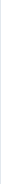由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和绍兴文理学院联合举办的“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学术研讨会5月10日至13日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举行,来自浙江、北京、上海、江西、河南、辽宁、内蒙古、重庆等地共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提交论文50余篇。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郑欣淼,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以及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广东省鲁迅研究会、广州鲁迅纪念馆等领导和单位发来了贺信、贺电。
在这次会议中,与会者主要就以下的内容进行了研讨,一是“鲁迅思想的越文化渊源”,二是“鲁迅与越地人物的精神联系”,三是“鲁迅作品的越文化表征”。
很多与会学者试图从“鲁迅思想的‘发生学’意义”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越文化对于鲁迅的深刻影响。王嘉良在他的《越文化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范式》中提出:“作为从越地走出的鲁迅,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背景在其生命历程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这是其生命的摇篮,也是其文化源头。”王嘉良着重从鲁迅的精神范式的形成来探寻越文化的深刻影响力,认为鲁迅从越文化中吸取了自强不息的独创精神,明清以降日益处于全国文化新潮位置的两浙文化传统造就了鲁迅的启蒙意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刚韧劲直文风中有最鲜明的浙东人的“硬气”。王晓初在《论鲁迅思想与艺术的越文化渊源》中指出:“在鲁迅看来,故乡越地的文化既有受专制主义压迫和封建伦理道德同化的沦落而流于浮滑的一面,也有被压抑被遮蔽被遗忘的特立独行刚健清新富有叛逆精神的一面,而正是这后一维面,构成了鲁迅精神结构和文学创作中一股潜在的涌流和一种支撑性的维度。”进而认为“越文化构成了标志着五四新文学确立的鲁迅文学的底蕴”。朱琼和黄健合作的《鲁迅对越文化的现代性继承与超越》首先从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指出越文化对鲁迅深刻的隐性影响,同时认为鲁迅对越文化有摒弃和超越。鲁迅对越文化的感受和体验是多重性质的,主要表现为鲁迅用现代的精神来洞察包括越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内部构造和逻辑程序,试图由此探寻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思路,他继承了越文化“艰苦卓绝、反抗强暴、忧国忧民的传统”,同时也以越文化中的落后层面作为批判中国国民性的现实起点。这是鲁迅对越文化的超越。陈建新和倪建伟在《鲁迅与越文化散论》中认为,越地的文化形态、文化色彩和成长环境都暗暗为鲁迅预设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场,使其在某个时候一旦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人学,个人主义的立场,它们就以一种强劲、深微的力量诱导鲁迅去认同、吸收这些异质文化而最终成就深邃思想。
黄岳峰在《鲁迅启蒙文艺观中的越文化源流》细查了鲁迅启蒙观中的越文化源流,指出越文化传统与鲁迅启蒙文艺观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试论鲁迅的越人情结及其民间意识》的作者王雨海则注意到了鲁迅的越人情结背后凝结的民间意识,具体表现为:鲁迅对越人精神和思想的接受角度在民间视野、野史趣闻;鲁迅喜爱统治阶级的叛逆者、对越地的民间风俗和民间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鲁迅将自我归入民间,反对偶像和崇拜;在创作中表现出与庙堂的对立和游离以及与民间欲望的一致性。竹潜民在其《湘中“山大王”与浙东“狼之子”》一文中从鲁迅与毛泽东的文化背景对比的角度提出鲁迅与浙东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有三点:一是韧性的复仇意识;二是务实的学术品格;三是深邃的历史眼光。进而提出毛泽东与鲁迅的心灵契合之处:故园情结、反传统禁锢、反理性模式。
在诸多学者强调鲁迅对越文化精华承传的同时,也有一些与会者提出越文化对鲁迅的负面影响,例如朱文斌在《风景之发现一论越文化对鲁迅的负面影响》中认为:“只论述越文化以优秀的一面(正面)影响鲁迅无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越文化落后的一面(负面)对鲁迅的影响更加深重。”作者以为,“阴郁、沮丧的消沉情绪一直伴随着鲁迅,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时代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时候,稍懂人事的他饱尝绍兴人的冷酷与势利,在心灵深处被播上了感受人生阴影暗面的种子。”朱文斌还“以鲁迅的婚姻爱情为例”,“可以看到,越文化的负面部分紧紧箍绕着鲁迅”。
鲁迅与绍兴先贤的精神联系,以前也为诸多学者所关注,本次研讨会中比较集中关注的是鲁迅与嵇康之间的独特关系。顾琅川、顾红亚的《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与嵇康》认为,把鲁迅与嵇康置于越文化这一共同的背景之下,可以发现两者在精神人格、文章风韵等方面的异同:精神人格都以峻烈不阿、磊落光明为特征而闪耀史册,但“鲁迅作为中国革命的伟人,其铮铮铁骨兼具有坚与韧两重特性,而后者,恰是嵇康所缺少的”;反传统反礼法是两者的共同点,但鲁迅更具自我的反思精神,体现出个性自觉的强者意义;在文章风格上强烈的否定性批判性怀疑性是两者共同的思想方法,简劲而富于骨力是两者相切近的语言风格。特别指出:“浙江这深刻一路文风由嵇康而一脉流贯到鲁迅,清楚显示出二人文章与越文化的密切渊源”。牟伯永在《鲁迅与嵇康越文化人格的同源性认知》中提出:鲁迅与嵇康具有文化人格的同源性,两者在精神品格、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等方面都表现出声息相通的特点。“究其原因,乃区域环境中固有的文化思想精髓通过文化的传承和民间的积淀影响该区域环境中士人的文化人格。而鲁迅对先哲的有意追摹,尤其对嵇康的浓厚兴趣,使鲁迅得以承续先贤超越先贤,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最卓著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革命的斗士。”
自北京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冷言鲁迅“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鲁迅与“绍兴师爷”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其后在鲁研界中却多语焉不详。直至上世纪末,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一书中提出:“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论战中,陈西滢曾经称鲁迅为‘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这显然含有大不敬之意。但我们如果排除论战中所特有的感情成分,作客观的考察,那么,应该承认,在思维方式与相应的文字表现上,鲁迅与绍兴师爷传统,确实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此后陆续地有若干文章和有关著论涉及此话题,基本观点与钱理群的看法大致不相左右。本次研讨会上陈越的《摆脱陈源的阴影一也谈鲁迅与“绍兴师爷”》,比较为与会者所注意。文章回顾了此话题近80年的历史,感慨于“鲁迅研究史在这儿呈现了一个怪圈:关于鲁迅与绍兴师爷的话题,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陈源那里!”认为鲁迅与绍兴师爷在思维方式或文字表达上确有某些相似性,但并不能以此断言鲁迅“继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陈文指出鲁迅对师爷并无好感;“师爷”在思维方式、文字表达上也难有“传统”可言,当然谈不上继承,而且在越文化的地域氛围中师爷仅是一个很小的职业群落,谈不上影响整体文化的气质,对鲁迅的影响也极有限;特别是鲁迅与绍兴师爷在人生道路的自主选择、人格表现等方面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鲁迅与绍兴师爷的某些相似性是因为“二者与越文化之间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都是越文化这棵‘历史之树’所结出的果实”。此外还有谢秀琼的《无法割断的文化链子一鲁迅对“师爷气”的认同与批判》认为,“绍兴师爷”作为文化链子上的一环,鲁迅对其“简括”、“察见渊鱼”、“字缝”的洞察、“反作法”的文笔,“多疑”的思维及“复仇”的心态有着肯定、传承的一面,也有对其身上因袭的传统文化陋习则有着否定、批判的一面。
鲁迅的小说散文多以故乡为背景,以虚实相间的“S城”、未庄、鲁镇等为典型环境解剖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生长于此的国民,同时也承载了鲁迅艰难的“精神返乡之旅”:一方面失望于“S城人的脸”,视绍兴为“棘地”;另一方面又无法舍弃心灵中对童年故乡的怀念,“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许多与会学者都注意到了“越地”在鲁迅作品中的复杂投影,注意到了越地风情对鲁迅作品的巨大影响。
裘士雄在《论周氏族群对鲁迅的影响》中周详地介绍了周氏三台门中的各色人等,并从“人生道路的选择”、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认识、“人物塑造的素材基础”等方面介绍鲁迅的家庭、周氏族群在“鲁迅世界”的重要意义。进而提出:“正是鲁迅在败落的周氏大家族、大家庭里,经历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才有利于成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佘德余的《鲁迅与家乡的戏曲艺术》注意到鲁迅在童年、青年时期“频繁地接触了家乡的戏曲和曲艺,童年和少年的生活记忆,生活积淀,为其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洞观人生,提供丰厚的素材和生活经验,也为我们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提供了契机”。
范家进的《依托和超越: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姿态》一文充分认识到“故乡”在鲁迅世界中的复杂性,一方面看到“越文化”的故乡在鲁迅作品中表现出的美丽场景,鲁迅对这些具有原始美的故乡人情人性的眷恋,以及地方文化对于鲁迅成年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依托意义和最初港湾;另一方面也体会到鲁迅在表现故乡时“处处渗透出一种对制约主人公人生道路与精神发展的地方文化氛围及社会风习的反讽、解剖、审视与批判”。这使得“越文化”背景具有了时代和历史的纵深,鲁迅的批判也从越文化中超越出去而指向整体性的中国文化。因此,他认为“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仅仅是解读鲁迅的一个分支,要避免“注意到其中一面而掩盖和遮蔽其中的另一面”。龙彼德的《论〈野草〉》则从《野草》中清理出浓淡各异的越文化特征:从《过客》中看到大禹,从《这样的战士》中看到勾践战斗的影子。从《野草》中还看到越地风景、风俗的描写和绍兴方言的运用。从中可以更深切地看到鲁迅“吾为越人,未忘斯义”的含义。邢晓飞的《走异路者的故乡回望》认为:越文化对鲁迅的乡土小说的创作给予了丰厚的滋养,它给了鲁迅小说以原料和毛胚,也对鲁迅的创作心理、风格造成一定影响。而鲁迅作为一个走异路的飘泊者,用在逃往异地的过程中形成的独到眼光、积累的学识和文化品格对故乡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人们的辛苦恣睢的生活进行了新的探查,剖析,从而铸造出了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而张直心《(在酒楼上)细读——鲁迅故乡题材小说系列研究之一》,用“细读”的方式,寻索“真实”后的“深”,悉心诠释那业已深化了的情感符号、精神意象。文章发现小说中的顺姑,已然是鲁迅记忆中的“重构”,是“旧日的梦”的肉身化,她透露着人到中年、入世渐深的作者精神的丝缕还牵着渐行渐远的故乡、童年、青春。
面对“商品经济”的现实,本次研讨会上也有了若干关于鲁迅的“应用研究”的文章,例如周一农的《当代越文化下的鲁迅品牌传播》,郑竹圣的《鲁迅介入绍兴旅游的背景及置景与价值》。前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实中的鲁迅遗产品牌化作了解读;后者则力求阐述鲁迅介入绍兴旅游经济的本因,认为现代文化在“释稀”着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经典文化,淡化严肃性,淡化意识形态,增强观赏性,增强世俗性。如今鲁迅介入旅游经济,使“走进鲁迅”更具大众化,其规模是空前的,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在“塑造人格”等方面的精神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成熟的显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中,视野的不断拓展显得十分重要,这是鲁学得以继续其辉煌的重要保证。“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这一命题的提出之意义正在于此。当然,其研究的深广度,还有待继续提高。
(晓松 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