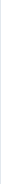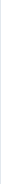鲁迅自幼便开始受到越地民俗、越地文艺、越地典籍以及越地民间文化的熏陶濡染。这种从小就耳濡目染的越地文化对鲁迅独立反叛和特立独行的独异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儿时的故乡记忆也成为他后来“思乡的蛊惑”和时时反顾的情感之源。不过,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家道中落后的现实境遇中,鲁迅更易于接受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和复仇精神的“剑文化”的影响,而当他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便又唤起了他对越文化中代表人之觉醒“书文化”的自觉发掘。从越地“剑文化”衍生出的反抗复仇的独异精神与越地“书文化”衍生出的个性觉醒意识便构成了现代鲁迅生成的内源性因素。
鲁迅与越地“剑文化”的亲近首先表现在他对越地典籍中野史、杂传的阅读上。尚在少年时期,鲁迅便看过《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越地文化典籍,因而对古越“剑文化”原型的勾践复仇故事非常熟悉。《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灭吴雪耻的这段历史,其中《越绝书》还被称为“复仇书”。鲁迅的《铸剑》等小说就是取材于这些他少年时读过的越地典籍,他曾回忆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

鲁迅与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复仇的“剑文化”的亲近,也与他幼时所受越地民间戏曲的熏陶有关。越地是一个具有浓厚鬼神信仰的地方,春秋以来,“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甚”。《越绝书》就曾记载越王勾践以巫作法,“覆祸吴人船”。正因为有信奉鬼神的传统和复仇精神的氛围,所以鬼神戏在越地乡间非常盛行。鲁迅在戏曲的氛围中长大,他非常熟悉民间演出的社戏、目连戏,特别是对《目连救母记》中的“义勇鬼”和“女吊”十分喜欢。在排演召唤越人起义战死者英灵的开场戏“起殇”中,鲁迅曾冒着被父母责罚的危险而上台演过“义勇鬼”。他也曾指出,“女吊”就是越地人民“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不仅熟悉也非常喜欢越地戏曲中这些带复仇性的鬼魂,尤其是充满复仇精神的“女吊”对他有着很深的影响,以致在临死前还与日本友人谈论起“女吊”。
由于自幼对越地文化中“剑文化”的亲近和喜好,少年鲁迅的身上也表现出一种“尚武”的性格。据周作人回忆,少年鲁迅就曾有过两次“尚武”的举动,一次是惩罚王广思的“矮癞胡”,还有一次则是去打贺家的武秀才。这些打抱不平的举动所显示的“尚武”性格,多少与鲁迅所受越文化中代表复仇、反抗的“剑文化”影响有关。在南京求学期间,青年鲁迅曾给自己取过“戛剑生”的别号。“戛剑生”意为舞剑、击剑之士。鲁迅的这一别号显示出他对越地“剑文化”精神的崇尚。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还曾有收藏刀剑的爱好,并珍藏过两把刀剑。此外,他还在浙籍留学生杂志《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一文,目的就是“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
另一方面,从绍兴到南京求学,再到日本留学,对古今中外书籍的“杂学旁收”使鲁迅在传承文化根脉和融化西学新知方面开始融合。虽然鲁迅当时离开了家乡绍兴,但是在他的意识深处一直存在着一个越文化的“场”。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化主张,表明了他开始有意识发掘传统文化的“固有之血脉”。他所谓的“别立新宗”正是建立在以近世西方文化的新知来激活以越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基础上的。所以在接受西方个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后,鲁迅便开始了对越文化中以人的觉醒为代表的“书文化”的开掘。
从留日回国到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曾有过近十年辑录古籍、整理古碑和抄写佛经的沉默期,而且他所辑录的古籍大部分都是魏晋时期会稽士人的著作或有关魏晋时期会稽士人的著作。对鲁迅来说,他“为自己选择了对他本身的研究来说是最佳的时间与空间,即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来辑录古籍。”他对包括《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谢承后汉书》等越地古籍的整理投入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对原籍会稽的魏晋名士嵇康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从1913年到1935年,鲁迅以二十余年的心血,择定善本,多次校勘,最终整理出《嵇康集》,以致“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

自从开始有意识地发掘和整理乡帮文献,鲁迅便产生了浓烈的“魏晋情结”,而他对魏晋时期越地的人物和文章尤为倾心。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走向个性自觉和文学自觉的重要时期,魏晋名士的“任诞”“清谈”正是人的意识的自觉。在魏晋名士那里,“药与酒里浸泡着人的生命意识中浓烈的苦味,人的生命又借药与酒之力迸发出不为名教扼抑的活力。”他们饮酒服药的惊世骇俗举动之中洋溢的是生命力的张扬,使那些在名教束缚下的卫道之士们黯然失色。
魏晋名士们所洋溢着人性本色的“魏晋风度”自然会染及文章著述。鲁迅曾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构想,并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魏晋六朝文学定名为“药,酒,女,佛”,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属于这部文学史的一部分。他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显然,鲁迅“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辑录故乡越地典籍建构了他当年“魂归故书”的“地域文化场”,一方面他得以从越地魏晋名士身上发掘觉醒的个性意识,另一方面他又从魏晋文章中获得文学观念觉醒的启发。
可以说,从对越地复仇反抗的胆剑精神的崇尚到对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与文章的钟爱,鲁迅对越文化的接受不仅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的熏陶濡染到自觉地回顾和发掘的过程,而且也经历了从早期的崇尚“剑文化”到后来的侧重“书文化”的变化。
本文转载自越地越风,作者为卓光平,素材版权均归原发布方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