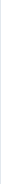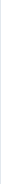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一个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但是这样的概念太过宽泛而失去了它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然而,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给文化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以至于威廉斯认为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难解的词之一[1]。文化的多义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任何一个普遍性的定义都不可能涵盖文化所有的内涵。不同的语境比如民族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俗文化等等,强调的是文化的不同侧面。因此,在文化研究中,首要的任务是厘清文化所处的学术语境,并进一步确定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 、越文化的研究取向及其意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文学科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各种学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等,纷纷与文化发生关系,从而使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彩的局面。那么,越文化研究作为地域文化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取向?越文化不可能囊括文化研究的所有内容,它必然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论者以为,越文化应将目光主要放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建立民族志的方式来建地方志,深入田野作业,考察越地“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2],以及现存的民风民俗、具有文化内涵的地名等等。格尔茨认为,“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及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3]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抽象的分析就是在进行文化阐释。文化在格尔茨看来就是人自己编织并悬挂于其中的意义之网[4]。对越地上述资源的文化阐释即构成了越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主要内容。
其二,对越地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包括越地传统(古代、近现代)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等等。在揭示越文化为中华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体察越地的精神特质与人文传统。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传统持有虚无主义的态度。近现代以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从西方汹涌而来,现代中国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来自西方。传统与现代被割裂。传统的失落使我们在无根的漂泊,从而导致了蔓延在社会各个层次的精神危机。寻找失落的传统刻不容缓。传统需要记忆、需要保存,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5]我们应该从目前的生活情境出发积极展开与传统的对话,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自我,在历史存在中发现自我。
越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越文化的考察,首先要辨别其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差异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丰富,而且展现了文化的不同表现方式。只有在具有特殊性的个体之间的对话,才能够真正向着普遍性行进。越文化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本文将目光聚焦于越文化的传统发掘,致力于东晋士人与越文化的特殊关系,以及越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越文化的另面
越人历来以尚武、怀疑、耿直等鲜明的个性著称。张兵认为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越文化的特征:“尚武爱国,创新进取,奉献自强”[6]。刚烈豪侠之气流淌在一代代越人的血液中,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善于接受新事物,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是越人又一特征,而在大禹、王充、陆游、鲁迅等人身上还有着自强不息,以天下为重的思想。这些都是越人展现给世人的不同于其他地域居民的精神特质。
但是,文化精神从来不会是单向度的,文化的丰富正在于它的多样性。在越人上述文化性格的背后,还有一种人们不太注意的文化特性,那就是东晋南迁士族带来的闲淡自然。潘承玉将越文化的主体分为五类,东晋南迁士族属于“由外地迁居于斯的越地新居民及其子孙”[7]。如果说生于斯长于斯的越人先民开创了越文化,那么越文化的保鲜与发展有赖于其他文化的汇入与融合。只有获得新鲜的血液,文化才会有创造力。越文化是一条奔腾的大河,与其他文化的交融就好像支流不断汇入。东晋南迁士族给越文化带来了不同文化因子的支流,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因子不同于主流越文化,可以说是越文化的另面,而正是这些另面文化丰富了越文化,使越文化呈现出立体化、多维化的的态势。
三、东晋士风文风的转变与会稽佳山水
东晋的士风文风与西晋不同。西晋士人无特操,追逐名利,他们的生活日益苍白,感情日益无力,文学上只有在辞藻排偶上用力;东晋士人则追求闲淡,无意功名,文学上或表现为枯淡或呈现出清新自然。
那么,东晋士风文风的转变原因何在?论者以为,这种变化与玄学有密切的关联。玄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文学中直接探讨玄理,从而使作品形成质朴枯淡的风格。这类文学是东晋的主流文学,后世对东晋文学的批判也主要是针对此而言。刘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8]。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义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尔”[9]。沈约指出东晋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是“寄言上德,托义玄珠”,而文风上则失去了遒丽的风格。遒,代表着魏代文学的风骨;丽,是西晋文学的主要风格。东晋文学将二者都抛掉,走向了质朴枯淡的风格。二是玄学的发展使东晋士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没有了建安士人建不世功业的大志,也没有正始士人的愤激,更鄙视西晋士人的追名逐利,他们所崇尚的是淡。正如王锺陵先生所说:“东晋一代的审美情趣,可以用‘玄淡’二字加以概括,而其核心则为‘淡’”[10]。
这种转变还受到东晋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影响。门阀政治使士族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庄园经济的发展使士族在经济上无忧。门阀政治和庄园经济为士族在生活上提供了充分的自由。东晋士人既无须考虑物质的需要,功名富贵又唾手可得,于是他们便转向精神,重视情性。
还有一点,这种变化与会稽山水有关。这正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
东晋士人既重性情,便喜在山水游弋中体悟人生。尤其要注意的是,东晋士人所处的山水是江南的秀丽山水,这种宁静秀美的自然山水的陶冶之下,他们的审美情趣、理性人格发生剧烈转变。东晋士人追求一种旷淡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旷淡,还是简淡,都是门阀士族具有浓厚玄学色彩的理想人格”[11]。东晋士人热爱山水,崇尚自然,对文学语言形式的要求也以自然为尚。所以,比起西晋文学来,东晋文学要质朴得多,形成了一种淡远清新的风格。东晋的文学理论不多,我们从李充《翰林论》中可以窥探其一二。《翰林论》现在只留下了残缺的几条,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校不以华藻为先”、“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12]。李充是东晋初期之人,他的文学观念已经不是西晋尚丽的观念。其论中多次提到的“远大”,这指对文学意境的的开拓。文学从魏代的动情与气骨,发展到西晋的繁丽;到东晋崇尚“远大”,总体文风表现为一种淡。
相对安定的环境对于文艺的发展是有利的,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家族的特殊地位,也特别重视文艺,所以东晋的书法、绘画等艺术都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第一流的。这些个人的修养如书法、绘画、音乐,同玄谈、文学一样是东晋士族身份的象征与显示。
身处江南的秀美山水,东晋士人重视在山水中陶冶情性。东晋社会,从帝王到僧人都在自然山水中追求一种会心。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3]。山水在他们的眼中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王徽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14]。顾恺之说,会稽山川“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5]。东晋士人认为山水自然中隐藏着宇宙、人生的真理。因此,士人经常出入于山水,王羲之、谢安、许询、支遁等名士名僧,“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16]。如果说竹林名士的放诞出于愤激,中朝名士则真的以纵欲为尚,那么东晋名士则转向为对个人修养的追求、转向山水之乐。
王羲之是东晋士风文风转变的典型。他归隐之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17]。在山水中,王羲之寻到了人生的乐趣。山水一直是王羲之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喜爱山水、崇尚山水。当时的会稽郡有佳山水,名士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士人用心去亲近山水、在山水中体悟玄理,将山水作为颐养身心之所。戴逵曰:“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斗。谅所以翼顺资和,剔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况物莫不以适者为得,以足为至。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澹泊之愿,于是毕矣”[18]。既然山水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士人就越发的喜游山水。
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19],王羲之召集同好在会稽山阴兰亭宴集。王羲之召集的这次三月三日的聚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共有四十二人参加。这次集会共辑诗三十七首,王羲之既是召集者,诗集序就由他来写。这就是他的散文名篇《兰亭诗序》。这样盛大的宴集在西晋也有过一次,石崇等三十人为送王诩还长安,共往金谷涧中,昼夜游宴,在石崇的别业举行金谷诗会,石崇曾作《金谷诗序》。时人将王羲之《兰亭诗序》与之相比。
石崇引以为豪的金谷别业,“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至”,又有水碓、鱼池、土窟,所谓“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众人“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在石崇等人的眼中,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水碓、鱼池、土窟等山水自然还只是各自孤立的“娱目欢心之物”[20],山水只是外在于人、让人娱乐的“物”。
兰亭集会中自然山水则显示了很大的不同。《兰亭诗序》开篇王羲之即点出聚会的时间和事由:“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21]。石崇《金古诗序》列举了若干可以“娱目欢心”的自然之物之后,便将山水抛之脑后,开始了热闹的诗会。王羲之对兰亭诗会的描述则完全不同,自然与诗会是相互交融的。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后,他开始关注山水:“崇山峻岭”是人所处场所,“茂林修竹”与“清流急湍”是人周围环境,“映带左右”象征着人与自然的无言融合。环境交代之后才是诗会的过程:“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同时描述诗会的过程中时刻不忘自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在这一段中,王羲之将诗会的过程与山水的描写始终结合在一起,此种安排富有深意。在这里自然不再是“娱目欢心”的对象,而是诗会中不可或缺、激发人思维和灵感的源泉,是诗人欢畅于其中,并与之对话、与之交融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人是自然的一个因子,人在其中领悟了生存的真谛。在山水中悟道并乐在其中,对于王羲之、及其诗友来说是人生乐事。
王羲之对自己闲适的隐居生活甚为得意。他可以在家中教养子孙享受天伦之乐:“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衣食之余,与亲人知交时共欢讌,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饮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22]。王羲之追求从容闲适,他本身又“一往隽气”[23]。他的这种气质表现在散文中形成了自然隽永的风格。这种文风正是东晋士人追求萧散的意趣、崇尚从容闲适的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
孙绰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他也善于在山水中悟道,认为山水是写作的源泉。《世说新语·赏誉》:“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不关山水,而能作文。’”[24]在孙绰的眼中关注山水是创作的前提,所以才会产生卫君长神情不关山水,而能作文的疑惑。孙绰对自己作文非常自信,本传曰:“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沙门支遁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25]
孙绰爱好山水,认为山水可以陶冶精神:“闲步于林野,则寥落之志兴”[26],“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己去,世事都捐”[27]。当人浸润于自然山水之中,旷远寥廓的自然山水与人内心之澹泊玄虚达到统一时,人便从中得到一种满足。正如黑格尔所说:“正确的观照和纯洁的心智只有在从现象中确实可以看到和感到现象所体现的本质与真理时,才获得满足”[28]。东晋士人喜欢山水,或亲临,或神游,都是因为他们在山水的真趣中获得了满足
兰亭集会,孙绰也是参与者,并作有《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王羲之文是前序,孙绰文为后序。在此文中孙绰认为,人处在不同的环境就会生出不同的情绪来:“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廖落之志兴”[29];他自己喜欢自然山水:“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这次身处“高岭千寻,长湖万顷”的三月三日聚会上,众人“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这种欢快的聚会使孙绰体悟到万物皆无差别的理趣。
可以说,正是东晋士人发现并挖掘了会稽的明山秀水,使山水逐渐走入文学的视野,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对象被观照,这对之后山水文学的大规模产生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也正是越地秀美山水促使东晋士人的审美情趣、理想人格发生了转变,他们的风度是真正的魏晋风度。于是,东晋士人与会稽山水碰撞结合,使得越地又生出这样一种闲淡自然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在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晋士人的风度更一直成为后世文人心期之所在。
[1]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页。
[2]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4]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6]张兵《越文化的特征》,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7]潘承玉《越文化研究纲要》,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8]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75页。
[9]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10]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97页。
[11]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页。
[12]李充《翰林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67页。
[13]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7页。
[14]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2页。
[15]房玄龄等《晋书·顾恺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04页。
[16]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72页。
[17]房玄龄等《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01页。
[18]戴逵《闲游赞序》,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50页。
[19]阴历三月三上巳修禊,是古人在水滨举行用以消除不祥之祓祭的一种形式。发展到后来仪式逐渐淡化,而演变为一种在河边嬉游宴饮的聚会。成公绥《洛禊赋》中“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禊,会同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艺文类聚》卷四)的热闹场面,正是对三月三日洛河修禊的记载。
[20]石崇《金谷诗序》,《全晋文》卷三十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51页。
[21]王羲之《兰亭诗序》,《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99页。
[22]王羲之《与吏部郎谢万书》,《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02页。
[23]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1页。
[24]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1页
[25]房玄龄等《晋书·孙绰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44页。
[26]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08页。
[27]孙绰《游天台山赋》,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28]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页
[29]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