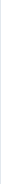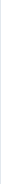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江南地区学术文化源远流长。南宋时期已经后来居上,远远超过北方文化水平。清代乾嘉时期江南文化达到中国文化高峰,出现“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的学术特征。清代江南文化的内涵并非仅限于历史考证层面,而是具有极其鲜明的学术理念。全面总结乾嘉时期江南文化的理念及其特征,不仅对于深入认识清代学术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具有深刻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研究乾嘉学术的人们往往把“实事求是”视为乾嘉学者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未能深入揭示其文化内涵。从清代江南学者对“实事求是”的阐释中,可以发现这个观念并非个别人所特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这充分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时期江南学者的头脑里,成为他们研治经史之学的治学宗旨。
乾嘉时期江南学者不仅把“实事求是”口号作为考据手段,而且用来作为其治学实践的指导原则。开乾嘉江南文化风气之先的戴震,首先阐明“实事求是”治学原则的必要性。他说:“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则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东原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凌廷堪认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即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事略状》)钱大昕指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把这一标准视为治学的最高原则。王鸣盛治史目的在于“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十七史商榷·序》),强调研治经史之学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赵翼评价朱熹《四书集注》说:“《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陔余丛考》卷四《四书别解数条》)这样做既不会掩盖前人创始之功,又可以看到后人新解之长,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意识。
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以评骘古今学者的学术成就。章学诚高度评价宋代朱熹、黄榦、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元代金履祥、许谦,明代宋濂、王祎,清代顾炎武、阎若璩诸人治学“服古通经,学求其是”(《文史通义·朱陆》)。钱大昕不但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奕、王应麟诸人“穿穴经史,实事求是”(《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而且称赞同时之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钱大昭治学“孜孜好古,实事求是”(《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三国志辨疑序》),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元史本证·序》)。梁玉绳评价钱大昕《汉书考异》“皆实事求是,出自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清白士集》卷二十八《答钱詹事论汉侯国封户书》)。洪亮吉赞誉邵晋涵“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这类评价在乾嘉时期学者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清代江南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就是要审视前人的学术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卢文弨指出:“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唐之为释文、为正义者,其与古训亦即不能尽通,而犹间引其说,不尽废也。至有宋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会冥契,独辟窔奥,不循旧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数、声音、文字之学,多略焉。”(《抱经堂文集》卷二《九经古义序》)王鸣盛治经迷信汉人,治史则没有禁忌。他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它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贬,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十七史商榷·序》)钱大昕评价史书记事是否得实,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二》)史家记载历史如果“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就必然造成历史记载的遗漏或史书记事的失真;倘若“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就必然导致伪造历史。上述两种“非实”情况,在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大量存在,需要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对于前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是否和真实史事相符,重在纠谬刊误。对于后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重在疑古考信。两者虽然考史旨趣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通过考证史书记载与客观历史是否相互吻合,审查史书记载的内容是不是“实事”,最终达到“求是”境界。上述情况表明,乾嘉时期江南学者的“实事求是”概念,并不只是治学特征或考据方法,更主要的是规范其治学实践的学术宗旨。
自宋明以来,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客观历史环境而空洞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或强立文法,予夺褒贬;或纵横捭阖,驰骋议论,其学术评论严重背离了知人论世的原则。这种文化氛围造成学术著述纰缪疏舛,历史评价严重失实,给学术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清代乾嘉时期江南学者在抨击前人治学虚妄不实的同时,以尊重历史和护惜前贤的自觉意识发覆纠谬,征实考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特色。
洪亮吉批评明季以来篡改古书的不良学风,指出:“以古人经世久远之文,斤斤焉刻以制艺绳尺,稍不得其解则从而易之,而点画、音训破碎错乱者,不可更仆数也。古人一字之疑,解至数万言,秦延君之于《尧典》是矣。今人疑则改之,曾无所顾忌。深虑此风一启,而学者遂人人自用也。故一二能读书好古之士,必远求宋元善本以为定式,非苟徇其名也,诚以古人之书为有明中叶诸君子颠倒错乱者不少耳!”(《卷施阁文甲集》补遗《上内阁学士彭公书》)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给后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灾难。洪亮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尖锐地揭示出明清以来史学中存在的弊病。他说:“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史,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加子云以新莽,削郑众于寺人,一义偶抒,自为予圣。究之而大者,如汉景历年,不知日食;北齐建国,终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赵师渊,至其后如明之贺祥、张大龄,或并以为圣人不足法矣。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于是为文士作传,必仿屈原;为队长立碑,亦摩项籍。逞其抑扬之致,忘其质直之方。此则读《史记》数首而廿史可删,得马迁一隅而余子无论。其源出于宋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后如明张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艺之法行之矣。”(《卷施阁文乙集》卷六《杭堇浦先生三国志补注序》)这两种类型的史论,其共同缺陷是不顾历史事实,肆意攻苛古人,形成驰骋议论的学术风气,导致历史评价偏离正确的轨道。
戴震认识到“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批评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妄加评论的不实学风,指出这种治学态度存在厚诬古人的危害。他主张采用汉人训诂方法揭示儒家经典的意蕴,追根溯源探究先秦儒家之道的真正含义。戴震认为:“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戴东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阐明了考据训诂与学以明道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钱大昕强调尊重古人本来面目,反对不顾客观事实而轻易訾毁前人。他指出:“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学殖无成,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主张护惜古人,尊重历史,大力阐扬求实精神。钱大昕特别强调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他认为评价别人应当具有辩证态度,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钱大昕指出:“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潜研堂文集》卷十七《奕喻》)这种自觉的理性精神,促使他最大限度地做到尊重古人的历史事实,在历史考证中能够深入肯綮,成为乾嘉历史考证学家中考史成就最大的学者。
王鸣盛对轻易褒贬历代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做法极其反感,强调说:“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乃是护惜古人的态度,可以保障学术继承与发展;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乃是文化虚无主义态度,终究会毁灭学术。他主张“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扬州刺史治所》,并在考史实践中广泛“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缺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十七史商榷·序》)。在王鸣盛看来,只有根据切实、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是著述,而那种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在护惜前人和嘉惠后学的精神动力驱使下不辞劳苦,反而觉得乐在其中,无怨无悔投入考史之中,付出了全身心的精力:“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盃,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饷太牢,不足喻其适也。”(《十七史商榷·序》)这是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把学术研究作为世代延续不断的神圣事业,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发展和完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指出:“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的认识在当时最具代表性,鲜明地反映出清代江南学者的文化价值观。
章学诚在治史实践中自觉坚持尊重前人学术成果的原则,阐明了朴素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和评价方法。他指出:“鄙人所业,幸在寂寞之途,殆于陶朱公之所谓‘人弃我取’,故无同道之争,一时通人亦多不屑顾盼,而鄙性又不甚乐于舍己从时尚也,故浮沉至此。然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强己量之所不及;知己学之不可以概世,而惟恐人有不得尽其才,以为道必合偏而会于全也。”(《章氏遗书·佚篇·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后人评价前人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又不可抹杀他们的功绩。章学诚认为:“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拾前人之遗。……而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文史通义·答问》)但凡心存求胜古人之事的人,虽然攻驳前人不无某些可取之处,但在主要方面却走向谬误,实属得不偿失之举,对于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他曾经参与修订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成就远出陈桱、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诸家同类著作之上。章学诚对此评价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于九源,乃有‘赐也贤乎,我则不暇’之诮,则谓之何耶!”(《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他没有贬低前人著作的创始之功,而是客观地指出上述诸家著作的成就和不足,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充和发展的结果。章学诚反对后学“轻忽先正苦心”,强调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保障学术文化能够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前提条件,这一思想达到中国古代史学认识论的最高水平。
邵晋涵研究学术也反对轻易评论古人,指出擅自立目褒贬史实的危害,批评范晔《后汉书》创立《独行》、《党锢》、《逸民》三传,实为后世史家多分门类的滥觞。他说:“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南江文钞》卷三《后汉书提要》)指出设类例褒贬,不如直书其事褒贬更有价值。他批评《新唐书》说:“使[欧阳]修、[宋]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南江文钞》卷三《新唐书提要》)意在说明史家把主观立类标准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以此对历史作出议论褒贬,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邵晋涵反对门户之争,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前贤。他一方面抨击宋明学术的空疏不实,另一方面也反对完全抹杀其历史功绩,曾经设想重新改编元人所修的《宋史》,与章学诚多次讨论改撰《宋史》的义例问题,要求修史不加褒贬,直书事实,最大限度地做到护惜古人,尊重历史事实。邵晋涵指出:“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即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章氏遗书》卷十八《邵与桐别传》)他鉴于元代史家修撰《宋史》受理学空泛议论的影响太深,拟取古代记事之书皆称《志》的本意,名其书为《宋志》,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历史真相。邵晋涵为毕沅修订《续资治通鉴》,具体贯彻了这个宗旨,修书时“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义”(《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样的史书既融入了史家认识历史的价值观念,又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历史的真实。
自南宋以来,江南文化中就形成了明确的“经世致用”治学主张。明末清初的江南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清代考据学的风气,具有鲜明的学术经世目的。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自觉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思想,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虽然谦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廿二史札记·小引》),但实际上正是暗示了自己要自觉继承顾炎武的治学精神,出其所学为社会所用。钱大昕评价赵翼的史学为“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廿二史札记·序》)。这话虽不免有过分推奖之誉,但也确实彰显出赵翼的思想中具有以史学经世的目的,而不是仅仅做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问。
王鸣盛以后人治《汉书》为例,指出:“三刘氏作《刊误》,而昆山吴仁杰斗南又作《刊误补遗》,是当为刊刊误矣。今予于吴氏再为饶舌,则又当为《刊误补补遗》矣。展转驳难,纸墨益多,岂不无谓而可笑!人生世上,何苦吃饱闲饭,作闲磕牙!”(《十七史商榷》卷七《刊误补遗》)他主张研究史学应当有益于社会,起到史学经世的作用。王鸣盛主张史书应当记载经世之文,否则对后人无用,终将失去学术价值。他说:“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传后。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李吉甫作元和郡国图》)根据这个标准,王鸣盛赞赏杜佑的《通典》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辞尚体要,切于实用,为经世之学。而对李延寿则予以指责,诸如“李延寿意主删削简净,乃其所删者往往关系典章制度、生民利病,而所添妄诞,则又甚多”(《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蒋帝助水等事》);“《南史》意在以删削见长,乃所删者往往皆有关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偶有增添,多谐谑猥琐,或鬼佛诞蔓。李延寿胸中本不知有经国养民远图,故去取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史书倘若只记载于世无补的琐碎细事,而遗漏或删削可资借鉴的重大事实,则对社会与人生价值不大。他还赞誉司马光等人所修的《资治通鉴》记事详实,“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洵不愧资治之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资治通鉴上续左传》)。他之所以把此书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就在于它对社会和对人生修养具有极大借鉴价值,可以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王鸣盛反对泥古守旧思想,对博古与经世的关系也有正确认识:“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悖,是谓通儒。”(《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关于“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治学目的,充分表明治史“经世致用”的意识非常突出。
钱大昕明确主张“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世纬序》)。然而后世儒家抛弃了先秦儒学务实致用的传统,渐渐成为空疏无用之学。他说:“夫儒之为世诟病者,自贵而贱人,自盈而拒物,一旦临难,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讲求性命,如小儿学舌,盲人说书耳,恶睹所为本原哉!”(《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二《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这种文化对社会没有实用价值,所以逐渐为人所厌弃,于世无补。钱大昕主张学者当讲求用世之学:“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为轻重;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当讲求经济,务为有体有用之学。”(《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河南乡试录序》)这样才能成为有本之实学,达到经邦济世的效果。他为江南崇实书院作记,也表现出明确的学术经世思想。书院的创立者“念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爰创立书院,以为造士之所,而颜之曰崇实。莅政之暇,辄招诸生立庭下,诲之以有本之学,务笃其实,勿逐于名,煌煌乎大儒经世之言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崇实书院记》)。他主张学术不能脱离现实,而应当学以致用,有益于社会。
汪辉祖对学以致用的目的认识非常深刻,治学注重实用。他说:“学必求其可用,凡朝廷大经大法,及古今事势异宜之故,皆须一一体究,勿以词章角胜。无益之书,不妨少读。”(《梦痕录余》)他结合自己佐幕的吏治经验,认为实学可以为社会提供治理措施。汪辉祖认为:“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每见幕中公暇,往往饮酒围棋,闲谈送日,或以稗官小说消遣自娱,究之无益身心,无关世务。何若屏除一切,读有用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佐治药言·读书》)他明确提出史学“经世致用”的主张,具有鲜明的学术为现实社会服务思想。汪辉祖辛辣地讽刺那些嗜古而不通今的人,认为他们于世无补。他说:“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有等嗜古之士,于世务一无分晓,高谈往古,务为淹雅,不但任之以事,一无所济;至父母号寒,妻子叫饥,亦不一顾。不知通人云者,以通解情理,可以引经制事。……否则迂阔而无当于经济,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世何赖此两脚书橱耶!”(《双节堂庸训》卷五《读书以有用为贵》)这足以说明汪辉祖对学问与致用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揶揄博古无用之人为“两脚书橱”,讥刺博古而不关心社会的学术风气,主张学问应用于社会,方为有用之学。这和刘知幾把他们比喻为“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史通·杂说下》),章学诚把他们比喻为“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章学诚把江南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特别强调史学的经世目的,旗帜鲜明地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章学诚认识到,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这是因为学术风气影响学者以特定价值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得失利弊;而人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学问最重要,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前人学术的臧否。他们的思想认识必然打上这种学风的烙印,形成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潮。章学诚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学者往往根据特定学术风气的价值观念品评前代学术是非,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颇之见,如此循环无穷,往复不已,导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无法看清前人学术的真实面目。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夫风气所在,毁誉随之,得失是非,岂有定哉!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往复,莫知所底。”(《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因此,学者应当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治学要有定见,不应当随风气为转移。而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就要求学者必须研究真正的学问,以学业作为挽救学术风气积弊的中流砥柱。他说:“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认识到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如果能够相互学习和相互补充,就有益于学术进步;如果相互仇视和相互斗争,则无法保证学术健康发展。他说:“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而农余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这不仅需要具备预见学术发展趋变的见识,而且需要具有为学术而献身的勇气。因为对于末世学风“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章氏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宫詹书》)。究竟是“持风气”扭转思潮,还是“徇风气”加重积弊,成为学者面临的艰难选择。然而学者治学只有敢于“持风气”而不“徇风气”,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促进学术乃至社会正常发展。
清代乾嘉时期的江南文化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即使对当今的文化建设也显得难能可贵,需要大力阐扬,认真加以继承。今天的学术界,尤其应该继承乾嘉学者的治学理念,弘扬其精神品格,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继承和发扬乾嘉时期江南文化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态度,有助于端正对“求真”与“致用”相互关系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每一种学术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学术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误。特别是在宋明理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文化几乎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对历代史籍不加以全面整理,势必严重阻碍学术的发展。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本着实事求是、护惜古人、嘉惠后学的精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全面清理前代的思想文化成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全面总结传统学术文化的需要。他们在当时整个学术界不仅引领风气之先,而且居于中流砥柱的地位,本着求实征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经史,一扫宋明学术末流空疏不实学风,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端正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代某些研究乾嘉考据学的学者把乾嘉文化看成只重“求真”而不顾“致用”,其实是一种偏颇认识。实际上,从清代乾嘉时期江南文化的治学宗旨、态度和目的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对“求真”和“致用”两者并没有偏废。认真借鉴前贤的这份宝贵遗产,可以使今天的学者更加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认识。
其次,继承和发扬乾嘉时期江南文化的学术理念和精神品格,有助于自觉抵制当前文化界急功近利等浮躁学术风气。清代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本着嘉惠后学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学术研究,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发千载之覆,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戴震考释《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被誉为乾嘉考据学的典范。钱大昕考证两晋南朝之际侨置州郡问题,追溯历史记载致误的源头,澄清了唐修《晋书·地理志》沿讹千年的谬误,成为清代考史成就的杰作。王鸣盛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删削失实,并且评价了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的失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是个人能力不同所致,主要是有没有自任其劳、嘉惠后学的精神在起作用。章学诚治学提倡“持风气”而反对“徇风气”,其历史意义已经超越了乾嘉时期特定的时代与空间,显示出历久而弥新的学术价值,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目前学术界存在的“泡沫学术”问题,已经给文化的品格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一系列危害,是敢于“持风气”挽救和扭转治学浮躁的局面,还是“徇风气”继续加重学术的偏颇程度,成为摆在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今天重温章学诚的治学见解,对于当前的文化研究一定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