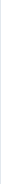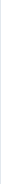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蓉,晚号定甫,别号离垢居士。先世本姓钱,原籍浙江长兴,自祖父辈值明季乱离,流徙江西铅山,为蒋姓嗣子,始改姓蒋。蒋士铨自幼家境贫寒,父亲精刑名之学,长年奔走在外,从小跟随母亲寄居于外祖父家,母亲教他认字,授以四子书《礼记》、《周易》、《毛诗》及唐宋人诗,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二十二岁为诸生,二十三岁举于乡,十年后得中进士。尽管蒋士铨殿试二甲十二名,朝考钦取第一名,但实授的是庶吉士,三年后为编修,以后虽一度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他声誉日起,名公卿争以相识,却多年居官不迁。乾隆二十九年(1761)深受乾隆器重的江西同乡、时任工部侍郎的裘曰修举荐他“入景山为内伶填词,或可受上知”,[①]而蒋士铨却“意不屑屑”,不原为显宦效劳,违背自己从地方官做起,实现兼济天下的宏原,于是一气之下,愤而辞职,治舟南下,侨寓南京。然而南京也终非久留之地,家乡又无田地可资生产,恰在此时,浙江巡抚熊应鹏致书延请他主讲绍兴蕺山书院。绍兴是明清时期浙东文化中心,王阳明、刘宗周和浙东史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皆活动于浙东。蒋士铨欣然同意,遂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夏应邀前往,翌年,举家侨居绍兴蕺山天镜楼,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担任扬州安定书院山长为止,中间曾到杭州崇文书院讲学两个月,曾返江西铅山祭扫祖墓,前后担任蕺山书院山长达六年时间。他悉心教授生徒,奖掖寒俊,为绍兴府培养了一批才学之士。在致力于山长份内事外,他还一再致书宁绍台道建议重修绍兴三江应宿闸和萧山富家池石堤,广交绍兴贤达,公馀,游览绍兴人文胜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积累了戏曲素材,为其后来的戏曲《桂林霜》、《冬青树》的创作作了准备。蒋士铨在绍兴期间,迎来了母亲在任上,儿孙罗列膝前,居住在风光秀丽的书院“天镜楼”中,面对如画的山川,和当地名士与生徒的交往,是其一生中感到最愉快最自在的时候,他曾在《还蕺山作》诗中写道:“鉴湖倘许赐臣老,杭州虽好吾能抛。”
蕺山,位于绍兴府城东北部,“山产蕺,越王句践从赏粪恶之后,遂病口臭,归国后尝采食之,故得名。晋王羲之曾于此卜宅,后捨宅为戒珠寺,故又名王家山、戒珠山。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戒珠寺宇泰阁为‘士子肄业之地,常千余人’”[②]乾道间(1165—1173)韩琦六世孙韩度隐居讲学于此,名相韩旧塾。明末,刘宗周在此讲学,名蕺里书院。后为优人所居,供唐明皇像于其中,号老郎庙。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府俞卿捐俸赎回重修,改名蕺山书院,置学田,延良师,持续近两百年左右。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全祖望曾应绍兴府太守杜甲之邀出任蕺山书院山长。乾隆三十一年六月蒋士铨至绍兴主讲蕺山书院,其《蕺山书院》诗写道:“採蕺人何在?当年内史家?桥存题扇迹,池剩浴鹅洼。万井当楼见,群山抱郭遮。地从人境别,心到上方遐。讲席依峰拓,名贤接重夸。……敢立名山业?先攻美玉瑕。修途相砥励,疑义共爬梳。伪体搴群帜,游谈绝众哗。……育贤吾道长,养士国恩奢。仆病归无用,人才信有涯。愿书忠孝字,朝夕语侯芭。”表示要全力教授生徒,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其《揭蕺山讲堂壁》云:“竭忠尽孝谓之人,治国经邦谓之学,安危定变谓之才,经天纬地谓之文,海函地负谓之量,岳峙渊渟谓之器,光风霁月谓之度,先觉四照谓之识,万物一体谓之仁,急难赴义谓之勇,遗荣远利谓之廉,镜空水止谓之静,槁木死灰谓之定,美意良法谓之功,媲圣追贤谓之名,安于习俗谓之无志,溺于富贵谓之无耻。”可见其非常重视对生徒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学业的教育:上面提到的“人”、“仁”、“通”、“廉”可视为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而“量”、“器”、“度”、 “静”、“定”、“功”、“名”则可视为修养方面的要求;同时也十分重视生徒的学业。“学”、“才”、“文”、“识”方面的要求。蒋士铨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儒家忠孝节义是其立身之本;儒家宣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是蒋士铨的行为楷模。他非常强调“君子所恃立身以立国与民命者,只此浩然正气耳”的人生目标,为此把它作为教育生徒的目标、方针,张贴于蕺山讲堂墙壁,让人明晓。他于乾隆三十年(1768)春应浙江巡抚熊应鹏之邀,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期间写的《杭州崇文书院训士七则》,针对当时“师既无道学相关之心,弟各负揣摩自熟之见”等“教与学之陋习”,提出“立志”、“洗心”、“道学之辨”、“择交之法”、“毋存菲薄万物之见”、“当存万物一体之心,”这不仅仅是对崇文书院师生的要求,更是对绍兴蕺山书院师生的要求,因为“训士七则”是其在蕺山书院任职一年半以后,赴崇文书院讲学时提出的,其中“教与学之陋习”和“立志”、“洗心”等主张,其实是其在蕺山书院山长任上的教育实践的总结和概括。他始终坚持将“立志”、“洗心”、“奋志纯修”放在首位,否则“若不知为学之本,专工文字,是自等于匠艺之贱,不过求其技术之可绐人而获利也。”反对单纯地研习文化知识。他主持蕺山书院一年半时间的效果,在《覆山左李大中丞清时书》一文中有清晰的反映。李中丞,即李清时,福建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从孙,乾隆三十二年七月迁山东巡抚。蒋士铨与李清时兄李清芳友善,故李清时盛情邀聘其往山东。“忽奉大人先生之名,遂兴泰山北斗之怀。岂厌故而喜新,实久静而思动。况执经开府,可长楫于君侯;而侍坐春风得取材于长者。”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赴山东,“爰草札以辞两浙中丞,遂束书而别山阴弟子,不料哄堂鼓噪,长跪两阶,伏地号眺,同声一哭。谓先生若去,誓以死争;倘来使强邀,便同仇敌。……某虽存不忍之心,已决必行之志。我则佯为许可,彼乃窥见本怀,群奔两邑之庭,双挽二侯之驾,曰:‘郡无太守,公须一行;人夺经师,我宁两立?’县令乃飞舆莅止,广文亦驰马来临。跪拜一堂,但增踧踖,唏嘘满耳,只益徬徨。”蕺山书院学生如此动情挽留,府县地方官员出面恳请,充分说明了蒋士铨在蕺山书院山长任上的工作成效深入人心。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蒋士铨至杭州欲转道山东,不料李清时病重,于是应浙江巡抚熊应鹏邀请,主讲杭州崇文书院两个月,后仍回绍兴主讲蕺山书院。
蒋士铨对书院的教学与管理要求严格,讲究原则,对生徒却平易近人,谆谆教导,和蔼可亲,师生之间情谊深厚。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下旬暂离绍兴回南京接老母写的《蕺山别诸生》:“结束归装五两轻,暂抛楼外越山横,平分小别关河意,一种斯文骨肉情。终岁勤劳归雪案,寒宵攻苦仗灯檠。依依定有相思梦,还逐江潮早暮生。”抒发了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学生钟锡圭,字介伯,山阴县蕺山人,曾至天镜楼蒋士铨家,“君携脡脯来,请业能黾勉”,并被蒋士铨“延为孺子师,三雏羽毛短”。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蒋士铨将赴山东应聘,“我欲挟君去,汗漫历东兖”,“我子君弟子,对泣废餐饭”[③]双方建立了深厚感情。钟锡圭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著有《西樵集》。学生余霖,余姚人,“谒我蕺山麓。涕出悲不任,谓公具手笔,乞为《雷门吟》。亡兄名余震,雷门乃其字。”“我为一一书,教义可云止。”《雷门吟》[④]乃应余姚秀才余霖之请而作。沈荣锴,字皆金,号宝庵,萧山诸生,著乐府古诗《应弦集》,蒋士铨为之作《沈生拟古乐府序》,又为之赋《沈皆金秀才荣锴洞庭烟水图》、《鄂清风波图再为皆金作》七律诗。李尧栋(1753-1821)字东采,世居上虞,后迁山阴赵墅。少喜读书,擅诗,为文敏捷。乾隆三十三年(1768)蒋士铨作《李二郎尧栋诗》称扬其“背诵六经如泻水,下笔春蚕食桑纸。骅骝之驹走千里,无人不道佳公子。学使心折冠一军,叹息儿子徒纷纷。……紫禁谁呼小太白?明年身惹御炉香”予以勉励。果然,李尧栋于三十五年中举,三十七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永乐大典》纂修,典试官,累官至江苏,云南、福建、湖南巡抚,云贵总督。为政识大体,以便民为本。创修《四川通志》,著有《写十四经堂诗集》《乐府词》《奏疏》等。宗圣垣(1753-1815)字芥帆,又字介马风,会稽人。少年时曾师从刘文蔚、蒋士铨,以诗画等交游。乾隆三十二年(1767),宗圣垣才十五岁,蒋士铨作《两闲人图为宗介帆童二树作》称其“静者有宗生,能闲思故清。两人方落落,万物苦营营。”又作《书宗芥帆诗本后》称扬其“才如溟渤阔,情与沧江深。遣意珠房贯行蚁,使笔春气来空林。……海内休悲宝意在,替人继起君其任。”认为宗芥帆是第二个商盘。三十三年,又作《宗芥帆红袖乌丝小照》,称其画“滴粉搓酥费揣摩,金钗相亚画屏俱。人生富贵寻常事,难得鬑鬑未有须。”还有《百字令·宗芥帆秀才听雨图》、《贺新凉·宗芥帆惜花起早图》、《贺新郎·咏美人题红图为宗芥帆作》等词。宗圣垣果然不负众望,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历官雷州知府,著有《九曲山房诗钞》。
蒋士铨六载于越,除悉心教授生徒,奖拔寒俊外,还致力于山长的份外事。“越郡为泽国,城中河流纵横,界画若棋局,其阔处可并三艇,狭仅容舠。自昌安门入,由斜桥至小江桥数十武,为城河孔道,两岸列市肆,货船填集,载者、卸者鳞鳞然,而行舟来往如激箭,每壅阻竟日不能通。究其弊,则白蓬空船,叠泊不散,以致阗塞。”[⑤]针对越中河流壅阻的状况,蒋士铨视自已也是越城居民,主动向绍兴太守张椿山上书,建议“饬一诚实小官,查丈附近河身,有稍宽者,押令空船分泊各岸,不得聚此一处,严禁叠泊,仍不时往查,犯者杖船侩总甲及船户。又立禁碑,大书深刻,嵌立小江桥下,永垂严厉。”表现了他已融入越城居民之中,切实关心民众的生活。
乾隆三十五年元旦,蒋士铨陪同绍兴太守张椿山前往杭州,途径萧山富家池海防,亲见富家池土堤千百丈,由于“海水侵蚀,沙岸偪堤只数里,风潮披猖,一堤如短垣,苟啮而踰之,越州数邑殆矣。”灯下与太守谈论,“若能建石堤三十里,则数邑田庐,万年安奠。然计帑十万,恐大宪难于入告,某慨然久之。”[⑥]第二天抵达院署,蒋士铨摆事实,讲道理,建议宁绍台道潘兰谷观察筹画决定,“与为请恤于他时,曷若预防于今日。”蒋士铨据老人言:绍兴“三江应宿闸石脚松动,坼罅如裂缯,虽两板层蔽,而奔澜激箭,透漏曳喷缕缕焉,及此不重加修建,他日之祸烈矣!”并数次向绍兴太守,宁绍台道上书,建议立即筹画修复。并一再申明:“某局外迂生,何关痌痒,猥以食越人之粟已五年矣,则视越人如一家焉。”拳拳之心,感人至深。《清代七百名人传·蒋士铨》也载曰:“乞体后,主绍兴蕺山书院,时越中富家池,三江闸,日久湮废,士铨力请大府,借帑营治曰:‘事虽非山长责,然食越粟,则视越人如一家也。”充分表现了蒋士铨关心民瘼,与民休戚相关的思想品格。
蒋士铨还热心参予绍兴地方的文化建设,以期彰扬传统的文化道德。余姚龙泉山王文成祠中,旧祀其父尚书公德辉先生于旁舍,不合礼制。乾隆三十二年经朝廷批准,迁尚书公主于文武享堂后宫,都人推荐蒋士铨作《移祀进封新建伯南京吏部尚书王公记》。蒋士铨推崇忠义,一生中服膺刘宗周、倪元璐,他曾说:“明末绍兴具宰相才者二人:一刘公念台,一倪公鸿室。”[⑦]乾隆三十二年,好友刘文蔚出其收藏的先祖刘宗周遗像,蒋士铨欣而作《刘念台先生像赞》:称其“历官十阶,八去其位,君子之仕也,故难进而易退。……进则建言,退则讲学,公自完其人。”[⑧]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好友平圣台出示其收藏的倪元璐古文手稿,交给蒋士铨说:“此吾乡先生倪文贞公古文,公玄孙安士秀才之藏本也。弗梓,将散亡。”为此,蒋士铨“集同志醵钱若干缗”,亲自过问,安排,“缮写定本,编定次序,择日开雕。”蒋士铨亲自为其文集作序,作跋并作传,称扬“公之文章,即公之德业也;公之气节,即公之功名也。”“是皆学道有得之人,故能明道、载道、达道,以殉于道也”[⑨]乾隆三十三年(1768)朱赓裔孙朱秉直出示其收藏的张岱《三不朽图》镂板,请蒋士铨作序,他欣然允诺,于序中称扬“越中山水清雄奇秀,代多贤杰,即胜国三百年中,禀扶舆清淑之气,赫然辉映丹青者,已若此之盛,其有裨于后学也,岂浅鲜哉”[⑩]同年,又为其先祖朱文懿遗像作《朱文懿公遗像赞》公正评价朱赓“览彼花石纲,讲官声琅琅。诛彼皦生光,相公言煌煌。保骨肉,正国体……谏行言听,所全实多”的历史功绩。为绍兴后学研究、学习乡邦文献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蒋士铨在《天镜楼销夏杂诗》中写道:“优游鉴湖长(任处泉太守),刻苦石帆翁(刘豹明经)。出处人皆老,悲愉境不同。西园萤照字,快园酒临凤。与我成三友,宁论达与穷?”这里提到的任处泉(1693—1768)名应烈,字处泉,山阴人,家居杭州钱塘县。雍正七年(1729)举人,明年成进士,改庶常,授编修,乾隆四年(1739)以忧归里,服阙后任南阳太守,后买山阴陆游快阁遗迹建宅,以诗酒自娱终老。蒋士铨《行年录》云:“是年(指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蕺山,得交任处泉应烈前辈,诗人刘豹君明经,山川如画,诗酒周旋,甚乐也。”蒋士铨曾作《快阁十赞为任处泉太守作》,赞曰:“山谷创之,放翁效之,处泉广之。其阁不同,其快相同。呼我山谷,呼我放翁,则吾岂敢?盖处泉之宫。”任处泉卒时,蒋士铨正在南京,回绍后,即赋《挽任处泉(应烈)前辈》前往吊赙,诗云:“得交前辈缘非浅,但见狂奴意辄欢。”说明他俩相交甚是相得。“青冥忽报神仙死,万壑千岩黯对愁。”对其去世甚表悲痛。他与任应烈交游时间不长,而与刘豹君来往则较久。刘文蔚(1718—1780):字豹君,号柟亭,山阴县城水澄巷人。青年时期与里中商盘、周长发等结“十子吟社”。未几,商、周得第出仕,而文蔚久困科举,后以优行升入太学。蒋士铨来绍任蕺山书院山长,刘文蔚主动与之结交;蒋士铨罹足病,刘文蔚亲自送上家藏的特制膏药,“惠我元璧膏,裂帛为摊溶。蒸如温泉沃,暖若松炉烘。”[11]蒋士铨长子知廉拜刘文蔚为师,刘文蔚与蒋士铨月馀未见面,即致梦想念[12]。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蒋士铨拟赴山东之聘,离绍之日,刘文蔚将珍藏的明末倪元璐所绘竹石画卷,刘宗周手书诗册等前贤墨迹四种赠送,蒋士铨特作《豹君以前贤墨迹四种赠行,谨受念台公手书诗册,倪文正画石卷子,即用册内题圆觉经诗韵奉谢》[13]。刘文蔚在指导知廉写诗过程中,对知廉习诗夸奖,蒋士铨对知廉要求严格,认为“豹君称许知廉诗太过”,为此,“以诗咎之”;刘文蔚告诫知廉,学诗要熟读经义,蒋士铨认为:“记涌汝何有,万卷同过客。手无朱丝绳,空说散钱集。”[14]说明了朋友之间相交非常真诚,真正达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乾隆三十二年(1767)刘文蔚营寿藏于山阴之小亭山侧杨家溇,属好友蒋士铨为之作生圹铭。他在《越州七子诗序》中称扬“豹君明经,为此邦老宿,与予投分,订忘年交,性情文字,相饷无虚日,因得罄读其诗,而叹浙东唐宋闻人风骚遗绪为不坠。”又在《越州七诗人小传》为其作传,称其“慷慨慈谅,与人交有终始,周急排难,至典裘鬻书,不少悔。平生教授里门,又曾主讲睢阳书院,南北知名之士出门下者,科第相继起,君独以明经老,称诗于鑑湖、兰渚间,海曲知君名者交惜之,而君洎自如也。”
平圣台,字瑶海,号确斋,山阴人。蒋士铨作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的《送平确斋前辈游嶺南》诗中有“结友二十年,岁月嗟荏苒”之句,可见蒋士铨与平圣台于乾隆十七年在京会试时已经相识。平圣台于十九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知县,累官知广州同知,乾隆三十三年丁忧回山阴,两人一见如故,遂频繁往来,“寻诗橹停戛,读礼门豁扂。宾来颐辄解,论出首俱颌。”三十五年服阙,仍返广东任,蒋士铨作长诗为之送行。又作《贺新凉·次韵题平确斋桐阴引凤图》词二首。三十六年春,平圣台将自己收藏的倪文贞古文手稿交于好友士铨,蒋集“同志醵钱若于缗”,亲自安排缮写定本。
童二树(1721-1782)名钰,字璞岩,二如,号二树,山阴人。年轻时潜心诗文绘画,与刘文蔚、刘鸣玉、陈芝图等结社。后客河南巡抚阿思哈幕聘修一省三十六州县志。善画兰、竹、水、石,尤工梅。乾隆三十二年(1767)冬,秀才宗芥帆将自藏童二树画梅图赠给蒋士铨,其后童钰族人童墨林又携二树梅画相访,蒋士铨高兴地写了《童二树(钰)画梅诗》,表示“我不识君见君画,每对梅花身下拜。”又作《百字令·童二树借庵诗意图》、《齐天乐·又题二树讨春小照》词,对童二树绘画艺术由衷赞美。
蒋士铨主讲蕺山书院之馀,遍游了绍兴的名胜古迹,如禹陵、卧龙山越望亭、飞来山应天塔、鑑湖之若耶溪、樵风泾、寓山,还与家人一起游览了吼山、兰亭,写有许多首记游写景诗作,如赞颂大禹的《禹庙》诗:
山河不改一碑存,尚有神雅(鸦)集庙门。万水朝宗才力大,五州陈列帝王尊。桑田已见沉江海,娰姓依然认子孙。赢得游人看窆石,年年风雨长苔痕。
此外,还有《吼山游记》、《游兰亭》、《游柯山寓园》、《禹陵》、《吼山》、《赤堇山》、《梅梁化龙歌》、《宛委山金简玉书歌》等,也有即景生情,感兴述怀的《去越州》五首(其一):
此诗写于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七。蒋士铨主讲蕺山书院已有一年半,深得师生信任。然而蒋士铨接到山东巡抚李清时之聘,盛情难却,不得不离绍前往。书院师生与绍兴府县当道也竭力挽留,为此出现了诗中所写的离别场景。又如《楼外》诗:
楼外群山皆不去,爱与诗翁朝夕聚。有时掩面云雾中,任我低迷无觅处。睡醒岚翠偎枕函,新绿入窗沾我衫。终年相对益缱绻,半日不见如饥馋。屋庐疏密树深浅,城廓周遭田近远。风光四序楼五楹,母子六人书万卷。酒杯一桁排阑干,全家小饮浮云端。风吹笑语落街市,下界仰瞩玄都壇。戒珠寺后万竹竿,绕我楼半翔青鸾。诗翁老丑怕人见,却被山灵细细看。
此七古诗写于乾隆三十三年之秋,时居绍兴蕺山书院天镜楼中,诗人展眼楼外,青山绿树环绕,一家六口,母亲钟令嘉迎来任上,儿孙罗列膝前,生活充实,精神快乐。他们全家一起游览兰亭、吼山,学生王生还为其与夫人张氏写夫妇小像;母亲钟氏曾作《越州》诗:“保邦凭智术,存国仗阴谋,吴越同归尽,胥蠡定孰优?川岩名郡列淳朴古风流。可惜田畴少,都人贵远游。”对绍兴府的地理风俗皆有独到见解。这是蒋士铨一生中自感最愉快最惬意的生活时期。此外还写有《还蕺山作》、《天镜楼家宴》、《天镜楼销夏杂诗》、《三山叹》、《悼双槐树》等。
蒋士铨对绘画有特殊的爱好和相当的艺术鉴赏力,在绍兴六载期间,写过不少题画的诗和词。如《鑑湖笛会图》、《书倪文正竹石画卷后》、《童二树(钰)画梅诗》、《自题黻珮偕老图有序》、《两闲人图为宗介帆、童二树作》和《贺新凉·会稽令舒淡斋小照》、《留客住·商次纴夜雨怀人图》等,其中不乏佳构。如为王元勋所绘的《画和合》诗云:
王元勋,字湘州,世居山阴,善画。俞蛟《梦厂杂著》卷七评其人物画曰:“身长径寸,面大如豆,眉目井井,神情毕肖;而佈景设色,直追元人。”蒋诗揭示了王元勋和合二仙之画呼之欲活的独特技巧。
蒋士铨在绍兴期间,还写了不少文章,如为好友,刘文蔚等写的《越州七子诗序》、《越州七诗人小传》,为前辈诗人商盘写的《越风序》、《宝意先生传》,为先贤倪元璐作的《倪文贞公全集序》、《倪文贞公传》、《锲倪文贞公全集跋》和山阴州山吴爚文作的《朴庭先生传》、为吴璜写的《入祀昭忠祠鑑南吴公传》、为女诗人胡慎仪写的《石兰诗传》等,此外,还有《刘念台先生像赞》、《朱文懿公像赞》、《后游兰亭图跋》、《揭蕺山讲堂壁》、《祷绍兴府城隍祈雨文》等。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一样,反对诗文创作“近时多诗人,大半杜荀鸭。可怜服败絮,外借锦衣幂”的[15]蹈袭,主张“洒然脱依傍”有所创新。其写景记游之诗,纵笔挥洒,逸兴遄飞,咏怀唱和之诗即景生情,境界开阔,气势恢宏,其词骨格清奇,缠绵婉曲。古文亦卓然成家,有传记、序跋、杂记、书札等。其传记所写人物或为前辈或为同辈,大多为亲朋故交,真切详尽,形式多样。如为刘文蔚等所写的《越州七诗人小传》系为合传,为女诗人胡慎仪所作的《石兰诗传》则是诗人行谊的诗传,行文之详略,记叙之繁简,因人因事而异,皆不乏形象和生动细节的描写。其序跋,主要是诗序和书画跋两类:如《柳村遗草序》既记叙其诗歌的卓尔不群,又悯其一生遭际坎坷,可视为何在田、刘大申两人的传记。《后游兰亭图跋》描写作者与刘豹君、刘达夫等十一人游兰亭的情景,图中人物各有不同的状貌、服饰、姿态,宛然在目,堪称神来之笔。其书札,大多为热心公益,不以“越位言事”为嫌,多次向当道进言之作。他在《再贻观察书》中说:“某局外迂生,何关痌痒,猥以食越人之粟已五年矣,则视越人如一家焉。”因而为萧山富家池海防,三江应宿闸之事言于浙抚,而且两次致书宁绍台道潘兰谷观察,力陈建堤修闸的利弊。绍兴城河中舟船阻塞,“失时废事,民间病之”,为此他致书绍兴太守张椿山,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作者这类书札,多是从事实出发,剖析利害,直陈得失,说理周密,辞气委婉,颇具说服力。
蒋士铨不仅是诗人,也是戏曲家。他十分重视从实地调查和乡邦文献中获取题材,《桂林霜》传奇创作的契机就是得益于乾隆三十六年,他由绍兴去杭州途中,经过西兴古驿,“驿有丞,狭隘迫蹴,蹩随马牛走。官斯者猥俗自厌,过客不顾焉。”[16]蒋与驿丞攀谈,得知驿丞即马雄镇之子马宏埙。马言曰:‘某久困一衿,鳏居二十年,家壁之,乞升斗微禄养子女耳,岂得已耶?“蒋士铨听后,大为感叹:“于戏,忠义之门,顾亦官此耶!”,“予闻而悲之”,乃作《桂林霜二十四出》。剧作叙写康熙初年吴三桂据云南谋叛时,广西将军孙延龄和吴三桂勾结,举兵逼迫巡抚马雄镇投降。马雄镇不屈,孙将马雄镇全家逮捕系狱达四年之久,后来吴三桂杀死了孙延龄,又劝马雄镇投降。马雄镇贤贞不屈,大骂吴三桂而死,其家属仆婢等二十多人皆殉难。剧作宣扬了马雄镇“半载空衙,四年土屋,冻骨饿殍纵横阶戺间;虎伥雉媒,蜮沙鱼餌,日除左右而屹然不动。呜呼,可谓极其难者矣”的忠义精神,同时也为忠义邪恶颠倒的社会现实愤慨不平:“苦做忠良何所利,君不见走正派的人儿吃尽亏。”“叹文毅孙儿官职蹇,只愁他哭倒西兴破驿前。”[17]这是一部悲壮使人感愤的爱国主义剧作。
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长达三十八出的《冬青树》传奇,主要描写文天祥与谢枋得抗击元军、宁死不屈的爱国故事。剧名《冬青树》,显然袭用了南宋末年临安都城沦陷后,元僧杨琏真珈发掘宋帝后陵寝,掠夺宝物,弃骸骨于草莽,山阴县义士唐珏痛愤之,乃集里中少年,收诸陵骨葬于兰亭天章寺之旁,并植冬青树以为标记。嘉泰《会稽志》、元代陶宗仪《辍耕录》皆有记载,越人皆能详述。蒋士铨将其在蕺山书院任上熟悉之事插入文元祥、谢枋得以身殉国的壮烈故事之中,专门谱写了《发陵》《收骨》《私葬》《梦报》四出,使《冬青树》传奇成为《藏园九种曲》中优秀之作。蒋士铨创作的戏曲戏剧性强,重视描写人物内心活动刻划人物性格,曲词本色而又华丽,曲白通俗流畅,大多为场上之曲。
[①]蒋士铨自撰《清蓉居士行年录》,《忠雅堂集校笺》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③]《将赴山左李中丞之招留别钟介伯锡圭秀才》,《忠雅堂诗集》卷十七。
[⑤]《移绍兴太守张椿山书》,《忠雅堂文集》卷七。
[⑥]《与宁绍台道潘兰谷观察书》,《忠雅堂文集》卷八。
[⑩]《前明越州先贤三不朽图像赞序》,《忠雅堂文集》卷二。
[11]《病足谢豹君馈膏药》,《忠雅堂诗集》卷十五。
[12]《豹君不相晤者月馀,念我致形夜梦,明晨入山欢然道故作此谢》,《忠雅堂诗集》卷十六。
[14]《豹君戒知廉苦吟当勤经义再寄叠前韵》,《忠雅堂诗集》卷十九。
[15]《久不见刘豹君寄怀两首叠前韵》,《忠雅堂诗集》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