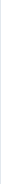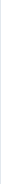潘承玉
我们很多人从小就接受一个观念,一提起封建社会,那就是反动的,一提起过去时代,就认为是万恶的。实际上,较之古人我们今天固然取得诸多巨大进步,我们的祖先也曾创造足以骄傲前人、无愧后人的文明。
我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如今正在各地各层次不断推进。但今天的学习型社会并不是突然冒出的东西,其实古人比如明朝的绍兴官员,也很注重学习。谈明朝绍兴官员的学习,就是穿越回到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从他们的智慧里汲取今人应该学习的思想与营养。
这里所说的“绍兴”,主要指明代绍兴的一府八县范围。如所周知,自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7年)“吴会分治”,新立治所在山阴县(当年越国都城,今绍兴市区)的会稽郡起,历经隋唐与北宋越州、南宋绍兴府、元绍兴路、明清绍兴府时代,近二千年间,萧山、山阴、会稽、上虞、余姚、诸暨、嵊州、新昌八县,皆属越国故都所在的行政中心管辖,明代这八县当然也是一个统一体。这里所说的“绍兴官员”,既包括外籍仕绍官员,也包括本土籍仕外官员,明代这两个群体声息相通,关系十分密切。这里所说的“在职”,包括在岗在职学习,也包括不在岗的带职(请假居乡)学习或临时罢职(很快起复原职)学习。
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主要方式
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方式,首先是自学。自学就是一个人苦思冥想,一个人遍阅群籍,一个人苦苦求索去探寻真知。这应该说是明朝官员,也是古代知识分子和今天一切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学习方式。比如王阳明以兵部主事疏斥宦官刘瑾,被谪贬贵州龙场驿丞期间,正德三年(1508)发生的“龙场悟道”,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钱德洪《王文成公年谱》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郭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自计得失荣辱”、“日夜端居澄默”、“中夜大悟”、“默记五经之言证之”云云,描述的都是自思自悟自学中常有的状态。
第二种以下属集体学习。首先是有固定场所的书院学习。如据《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十八《名宦后•南大吉传》记载:“嘉靖初以部郎出守郡……时王文成公讲明理学,大吉初以会试举主称门生,犹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悔,执贽请益文成。……乃葺稽山书院,创尊经阁,简八邑才俊弟子,讲习其中,刻《传习录》,风示远近。文成振绝学于一时,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皆大吉左右之也。”王守仁撰《尊经阁记》云:“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可见,陕西渭南人南大吉到绍兴来做知府,在如今的府山西坡翻新重建稽山书院,让山阴知县、洛阳籍吴瀛具体负责重建工程,初衷是出于自己对阳明心学初“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悔,执贽请益文成”的需要,才推己及人,“简八邑才俊弟子,讲习其中”,让绍兴府下面8个县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来稽山书院,听时任兵部尚书、回乡省亲的王阳明讲学的。显然,在这样的书院中,和王阳明一起探讨良知之学的,不仅仅“八邑才俊弟子”,还包括绍兴知府南大吉、山阴知县吴瀛等一干绍兴在职官员在内。也应该是绍兴全境缙绅阶层对阳明心学的这种热忱研讨、传承、尊崇,对远近产生示范效应,才使“文成振绝学于一时”,产生“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的四方来绍求学盛况。
第三种叫仕学所学习,这是专门讨论为官之道的集体学习。大家都熟悉《论语》上的两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历史上曾引起无数的讨论。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对这句话有一个解释:“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做事、做官做的好,再学习,一定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做事、做官;学的好,再去做事、做官,一定可以检验和深化所学。万历十一年(1583),绍兴知府萧良干把这两句话落实到行动上,在原来的稽山书院旁边办了一个仕学所。《万历绍兴府志》卷十八《书院•府城内•稽山书院》附载其《仕学所记》说:“始吾之学于家也,严惮有师,切磨有友,日置其身于圣贤载籍之间,而世故无所入其胸臆;然且作焉、辍焉,若或恣焉。今之仕也,肆于民上,所颐指而气使,皆畏我也者;所奔走而趋承,皆顺我也者。利禄荣名之私,日眩乎其中;而赞毁讥谗、荣辱得丧之故,又时时相寻于其外。吾于此其能无忽心乎?能无羡心乎?能不恶怒而动摇矣乎?吾虽时觉之,而倏忽兴仆,莫能自必者岂少也?吾兹进而与诸生聚讲于斯也,吾心惕焉,若寐之醒焉、豁焉,若滞之决焉;向之忽者、羡者、恶怒者、动摇者,不俟规诲,不烦言说,毛竖骨竦,与汗而俱出也。已一会聚,则一警策;愈警策,则愈凝定。……故吾孳孳进诸生而会也,若将以化导诸生,而岂知吾实藉诸生以为鞭影哉!……吾之名堂也,盖以自况也。”可见这是绍兴主官和在学诸生的集体学习,借以始终保持自我警惕和自我完善。
第四种是学社学习,这是无固定场所却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集体学习,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学会或研讨会学习。比如据陶望龄(号石篑)《证修社会跋语》等文献,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由时任云南参议、归乡省亲的嵊县周汝登主持,时任翰林院编修、同样归乡省亲的会稽陶望龄襄助,在府城北阳明祠成立的证修学社;据刘宗周《同心册序》、刘汋《刘忠介公年谱》,有天启五年(1625),由时任通政司右通政的刘宗周,与其表兄沈中一在蕺山解吟轩成立的同心学社;据《刘忠介公年谱》,有崇祯四年(1631),由时任顺天府尹刘宗周,与时任广东肇庆府推官陶奭龄等,大会绍兴缙绅学士二百余人,在绍兴府城江桥成立的证人学社等。其中,《证修社会跋语》载,“耳听目览之谓证,手持足运之谓修。……越,二王子(王阳明、王畿)之乡也,自龙溪殁而讲会废。钱君、刘君与同志若干人,始缔为社,名曰证修,而谒海门(周汝登)子主之;以仆之辱交于海门也,令书一语于册后”,云云。《同治嵊县志》卷十三《乡贤•周汝登传》对此也有记载;并载在这之前,出任南京兵部主事、郎中期间,周汝登积极参与当地的学社研讨,那时就是学坛的执牛耳者了:“南都讲会,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汝登为《九解》以伸其说,弟子日益进,执贽者千余人。”
“学惟学人乃真”,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内容
那么,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内容是什么呢?主要主题是讲“怎么做一个人”。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儒家的“儒”字,就是一个单人旁,《说文解字》说“从人,需声”。其实,“需”不仅代表声,也包含了义。怎么样做一个人,如何脱凡入圣,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考虑的问题。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其主要内容也在此。《传习录》说:“圣贤可期先立志,凡尘未脱谩言心。”要做圣人,就要摆脱你的凡尘之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冷静的想一想,到目前为止我做人有哪些缺点?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社会有哪些不良的风气?我沾染了几条,一二三四列出来。我今天反省,明天再改正,每天如此,慢慢地就做了圣人。
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成圣人,有的人只能成为普通人?王阳明认为,这是因为有的人能立志向学,有的人不能。《传习录》说:“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只要你立下做圣人的志向,迈开学习的那一步,你就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在绍兴、余姚,在贵州、江西,所到之处都和他的学生或者部下一起讨论,主题都在叫人要有向善之心、成圣之志,天天反躬自省,焕发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且注意随时加以鼓励。《传习录》记载,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来自苏北泰州的王艮出游回来,王阳明问他,你外出一趟看到了什么呀?他的学生回答,“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回答:“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王阳明又问另一个学生,来自杭州湾北岸的海盐董澐看到什么奇怪的事没有,这个学生也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就是这有什么奇怪的,你看看大家都在规规矩矩的做事,人人都很善良、纯朴、勤劳呢,真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
《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纲的终极之纲是至善,至善即做圣人,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宋代新儒家张载有所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愿意这么做能这么做的,当然也都是圣人。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到他对中国知识阶层的观察:“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所以,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学习主题都在追求道德的完善,都在探求如何成为一个圣人。孔子的学说是这样,王阳明的良知心学是这样,周汝登的证修学社、刘宗周的同心学社、证人学社等,无不如此。
《同治嵊县志》卷十三《乡贤•周汝登传》即载周汝登以云南参议归里期间:“与会稽陶石篑及郡士,会于阳明祠曰:‘阳明遗教具在,正当以身发明,从家庭间竭力,必以孝弟忠信为根基,勿为声色货利所玷染,习心浮气,消融务尽,改过知非,丝毫莫纵,察之隐微,见之行事,使人知致良知之敎,原如是也。’”《刘忠介公年谱》载刘宗周在同心学社成立仪式上的演讲及其反响:“先生痛言:‘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座中皆有省。每会,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柢凝定,为入道之基。”所谓“以孝弟忠信为根基”,使“习心浮气,消融务尽”,所谓“明人心本然之善”,“使根柢凝定”,均在通过学习引导大家做一个道德纯粹的圣人。刘宗周《证人社约檄》说的更明确:“盖闻学惟学人乃真。人与人同斯大,圆首方趾,何以等藐类于乾坤,古往今来,胡独拒吾生于贤圣?三复遗编,慨焉永叹!羲皇有作,首原性命之宗;尧舜相传,遂阐危微之秘。迨群圣人没,而一中衍派,委王统于衰周;幸吾夫子兴,而六籍还儒,表微言于长夜。……生于其后,能无景行之思?出于其乡,宁免过门之憾?……矧伊人兮,所学何事?如旅未归,深迷既往之途;似筑有基,先立只今之志。”好一个“学惟学人乃真”,“胡独拒吾生于贤圣”,“先立只今之志”!如何立志做一个圣人,才是一切学习的真谛所在!
绍兴地区的学者和千百年来的大多数官员和知识分子一样,学习的根本主题就是如何排除自己的私心杂念和这样那样的缺点,让自己超越一般的庸众而成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内在动力
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压力。内在动力就是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学霸,都是拼命的学习机器,在成为官员之前就已上紧无数圈的发条,成了官员之后很难停止下来。
古代的官员是怎么样“炼”成的呢?就明朝而言,官员的来源主要是进士、举人、贡生三途。考中进士,取得体面做官资格;考中举人,取得任低级官员资格;被考选为贡生,经在国子监三年以上深造出来,有资格充任“率以簿书升斗之吏畜视之”(《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语)的教官。要成为进士出身官员,必须先后通过童生→秀才,秀才→科举秀才,科举秀才→举人,举人→进士这四大考试环节。首先是童生变成秀才的童试,也就是说你在私塾、社学、义学等等基层学校里学习,学到差不多成年,需要经过县试(知县主持)、府试(知府主持)、院试(省提学道主持)三级考试,都成绩优等才能变成县学的秀才。一个县童生可能有2万个,甚至5万个、10万个,可是县学秀才的正式名额一般却只有20个,加上增生、附生,有时会有数百,也不会太多。根据文献,童生成为秀才的比例普遍不到5%。例如,根据时人叶梦珠《阅世编》卷二《学校一》记载,明末南直隶上海县,“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三年岁、科两试,“科入新生每县六十余名,岁入稍增至七十”,如果把“稍增”理解成“又增”,则三年经岁、科两试,从3000童生中总共录取秀才130人,录取率为4.33%。同时稍早同属南直隶的歙县,万历初做过浙江巡抚的邑人方弘静《素园存稿》卷九《辅仁文会录序》载:“万历丙申(二十四年,1596),邑之应试者凡二千人,邑试之,府试之,台使者又严试之,其得进于庠者仅七十又二人,难矣。”2000人录取72人,录取率为3.6%。《素园存稿》卷十《尊敬会录序》又载:“岁庚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邑之士应试者几三千人,有司者三试之,三选之,其进而肄业于庠者,七十有五人耳,盖其难也。”3000人录取75人,录取率低至2.5%!我们看其《千一录》卷十三又说:“以吾邑言之,儒童应试者三千余人,其得进于庠者七十人耳,富者之竞、贫者之滞,无惑也。”足见童试录取率2.5%,在歙县一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比率;准此以观,在其他地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儒林外史》描写周学道主持童试,最后一个点进范进,只见“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样貌简直惨不忍睹。小说接下写,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小说中此刻的范进,可以说是明代无数成年知识分子挣扎在童试之路上的命运写照。这还仅仅是士人成就功名的第一道关卡童试通过率的严苛情况。
明代,并非每一个秀才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秀才还得成为科举秀才,才能参加下一步的举人录取竞争。秀才要成为科举秀才,需在县学里学习满三年;期间每月要通过县学学官组织的月考,每季要通过府、县官组织的季考,每年要通过省提学道组织的岁考和最终的科考,所有关卡考试都名列优等,才能成为科举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举人考试。这第二道关卡,秀才成为科举秀才的科考,其录取率是多少?万历十五年由浙江巡按转任应天督学的江西人詹事講《詹养贞先生文集》卷一有篇《酌处贡途疏》,内中根据他对应天府各属府州县生员的科考所见,与对既往分配录取名额的反思,向朝廷报告说,隆庆间科考“有六人选一之例”,万历以来,“南畿郡邑人才多寡固殊,而科举人数亦甚悬绝,多者五六十名,次者三四十名,又次者二三十名,其下邑僻县有仅仅十余名者,有寥寥四五名者,此固旧额”,“臣则见南中邑学之多者不过三四百人,而最少者亦不下百余人;彼其三四百人者科举动经五六十人之数,而百余人者仅取四五人、七八人”。“六人选一”,即录取率16.7%;“三四百人者科举动经五六十人之数”,按400人录取60人算,录取率15%;“百余人者仅取四五人、七八人”,按100人录取6人算,录取率为6%。这是应天府的情况。我们再看其他地方。隆庆、万历间出任惠安知县的叶春及,其《石洞集》卷四《惠安政书三•班籍考•正纲》列有“季考生员约三百七十八名”、“察院按临考校生员每次约三百七十八名”、“提学道岁考生员约三百七十八名”、“应试生儒六十一名”各名目下开支经费,从此名目本身可知,晚明福建惠安县儒学在学各类秀才员额378名,“应试生儒”即每科科举秀才为61名,则该县秀才的科考录取率为16%。综合这些文献,明代可靠录取率总体约在12%,也就是100个秀才中间只有12个人有资格参加举人考试。
这样,一个成年知识分子要取得参加乡试资格,成为科举秀才,其可能性就只有5%(童试录取率取最大5%)、12%这两个比例的相乘,即0.6%。这还什么功名都还没挣上。再往上,科举秀才考中举人也就是乡试,举人再考中进士也就是会试,老是考不起举人的优秀科举秀才被选拔为贡生,这后面每一道关卡的通过率,又均远远低于童试、科考的录取率。①一个人能成为官员,他一定是战胜了无数的竞争对手,一定是个学霸。
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显著成效
首先是推进治理。学习的主题是做圣人,好像是句空话,但做圣人的途径却是具体的;特别是阳明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强调在实践中“致良知”,强调“察之隐微,见之行事”,这就把学习的归宿落实到从政行为上。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明朝认真学习的绍兴官员,都在管理绍兴地方政事方面取得卓著成效。比如南大吉,就修建了绍兴大禹庙,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禹陵”三个字是他亲自书写的;扩建了曹娥庙,表彰全境节烈女性,拿她们来配祀;修建了绍兴府城的楼堞;疏浚了绍兴的府河、运河和若耶溪,打通了绍兴府城内外的水系。王阳明就为府河的疏濬撰有一篇《濬河記》,对南大吉的敢于善于干事,造福于民,加以表彰:“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蓄泄既亡,旱涝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子乃决阻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謡之曰:‘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厉民欤?何其谤者之多也。’阳明子曰:‘迟之,吾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湖龟坼,越之人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
第二是形塑清廉。比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二《乡贤三•理学》载:“季本,字明德,会稽人。……师事新建,获闻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旧学而一意六经,潜心体究。久之,既浸溢,惧学者骛于空虚,则欲身挽其敝,著书数百万言,大都精考索,务实践,以究新建未发之绪。历仕与处,从游者数百人。……召为御史,以言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长沙守。……归二十余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禅林,以著书谈道为乐。”过去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位从“师事新建”走到“究新建未发之绪”的阳明心学学者、进士出身的长沙知府,却老来在寺庙里借住,连家都没有。还有陶大临,绍兴陶堰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榜眼,万历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历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货真价实威高权重的大官。《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一《乡贤二•列传后》载他,“貌不胜衣,而识沉守介,屹然不可动摇”,“于取予尤严,无论金帛,即书画名玩之遗,必峻却之,泊然无所好也。卒之日,槖无嬴金”。王世贞为撰《陶文僖公传》,内载一“奇事”:“尝迎韩淑人养于邸,得疾卒,公以丧归,……故陆都督柄方重,伺公窘于棺,遗之美材。”如此大官,母亲去世,连像样的棺材都置办不出!张岱曾祖、隆庆五年(1571)状元张元忭, “平生雅志圣贤,其学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颛务以实践为基”,“持操端介”(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本传),万历初官居翰林院修撰时,曾邀请生活窘迫的徐渭进京,谁知后者除了像在绍兴一样卖文为生外,并无任何秋风可打、油水可揩,以至在《与柳生》书中说:“在家时,以为到京,必渔猎满船马;及到,似处涸泽,终日不见只蹄寸鳞,言之羞人。”又在《与道坚》书中称:“今之入燕者,辟如掘矿,满山是金银,焚香轮入。命薄者偏当空处,某是也。”最后只好拂袖而去。还有一个会稽王舜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官刑部、兵部郎中、四川参政、陕西右布政、吏部侍郎,拜工部尚书,《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三《列传后》载他,“劳瘁竟卒于邸舍,萧然四壁,榻前一敝簏,书数卷,无不叹服其清云”。明代,做到六部尚书,也就是位极人臣②,但这位位极人臣的王舜鼎,去世时竟一无所有,只有破书篓子里的几卷书而已,至死都是书生本色。
第三铸成强者。以上两点就是今天所说的干事、干净,做官造福、为政清廉,但要做圣人,能干事、干净还不够,还要做一个强者。圣人是要敢于抵抗压力的。因为学习,绍兴官员成为明代中晚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最杰出的一批强者。从正德朝的反对宦官刘瑾,嘉靖朝的反对奸相严嵩,到天启朝的反对宦官魏忠贤,酷爱学习的绍兴官员一直都是举世瞩目的铁骨铮铮人物。例如,反宦官刘瑾,绍兴有王阳明和其姑父牧相,勇敢地站在前列。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一《乡贤之二•列传后》载:“牧相,字时庸,余姚人。少受业于王尚书华,华器异之,妻以女弟,令与文成公同学。弘治己未,遂与文成同举进士,授南兵科给事中。时逆瑾擅权,流毒朝野,相偕给事中戴铣,疏其不法数十事,忤旨械系赴京,廷杖九十,绝而复苏,下锦衣狱,时文成为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得罪系狱三月,相禠职为民,文成谪龙场。”反对奸相严嵩,有“上虞四谏”、“越中四谏”等绍兴士人是全国的急先锋,并付出惨重代价。这里只看严嵩发迹伊始,“上虞四谏”中两个并不太显赫的人物。《明史•谢瑜传》载:“(嘉靖)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礼、南巡盛事为解,而谓诸臣中无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圣怒,奸状显然。……居二岁,竟用嵩为相,甫逾月,瑜疏言……又三载,大计,嵩密讽主者黜之。……瑜遂废弃,终于家。……与瑜同县、同举进士,以劾嵩得祸者叶经,……嵩为礼部,交城王府辅国将军表柙谋袭郡王爵,秦府永寿王世子惟燱与嫡孙怀墡争袭,皆以重贿遗嵩,嵩受而许之,经闻即劾嵩。……又二年,经按山东,监乡试,及试录上,嵩见发策语多忤时,因指为诽谤……逮赴京,既至,系诏狱考掠,复廷杖经八十,斥为民,竟以创重卒。”
第四成就学术。学习学习,追根到底也还要成就学术。古代几乎没有专业学者,今人所知古代各种学派、学术思想,大多是从事其他实际工作者特别是官员的在职副业。明代绍兴官员在这方面又是举世难匹的典范。纵观明代学术思想史,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学派,五百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学说,孔子、朱熹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学派——阳明心学,及其浙中王门学派,儒学史上最后一个纯儒学派——蕺山学派,均为绍兴官员通过在职学习、研讨所创,这是特别了不得的,因为伟大的思想学术派不仅是所在时代的灵魂,还会深刻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
对明朝官员学习处境和不足的体认和反省
明朝已经过去400多年。明朝绍兴地区先人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及其圣贤可期、坚韧不拔的心路历程,还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回味;但包括绍兴官员在内整个明朝官员的学习处境或曰生存境遇,以及他们学习中存在的不足,也需要后人去做比较深切的体认和反省。
首先,明朝官员的学习处境或曰生存境遇是相当严酷的。一般人以为,宋朝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职官员的黄金时代,元朝由于长期废除科举和民族歧视政策,是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时代;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王朝,中国知识分子又从地狱重回天堂。但正如朱元璋腰斩高启,粉碎东南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幻想一样,核诸明代史实,这一判断也极不可靠;明代知识分子和文职官员差不多仍然活在一种精神地狱之中,只不过元代是显性的,明代是隐性的。明代知识分子读书仕进可能性之低,绝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其实都处在《儒林外史》所写范进“进学”之前的潦倒穷困状态,是表征之一;官员编制之少,任职责任之重,俸禄待遇之低,违法风险之高,是另外四大表征。如以一个县的范围来说,除儒学教官3名(教谕1员、训导2员)外,明代国家规定全县正式官员只有知县1员、县丞1员,主簿、典史各1员,总共4人;这总共4人,却要承担全县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人口社会的运转和治理③,可见其工作压力和负担之重。但全县四个官员之首,一般还都是进士出身的知县,明朝后期其法定月俸却只有米1石、布0 .325匹④。 故《明史•食货志六》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但法网森严,对大多数人来说,又无法谋求法外利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记载,正统六年(1440),光禄寺卿柰亨,堂堂的光禄寺一把手、从三品的大官,被自己的手下、从七品的该寺署丞张冕上本揭发,盗取供祀的猪鹅肉、面食私用,两人当场对质,最终得到皇帝“尔为堂官,贪饕如此,论法难容,姑宥之”的亲口斥责,也是宽容加羞辱;万历十八年(1590),反过来,光禄寺署丞茅一柱,又被光禄寺一把手上本揭发盗署中火腿,被问徒为民。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作奸犯科和“反腐”纪录。明朝官员的在职学习,除了力做圣贤这一主观上的崇高动机,客观上也是为了通过不断的学习,以排解做官责任繁重却待遇微薄、风险重大等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内在困境。但国家如此刻薄对待知识精英,有形无形造成知识精英的命运悲剧,既影响他们学习效能的发挥,更摧残他们的人格,压抑他们的创造活力,反过来又会给明朝国家造成悲剧。
其次,和当时所有其他学者一样,明朝绍兴官员的学习主要学的都是伦理和人格的完善问题,不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也不涉及经济问题,探究的都是哲学、道德问题,造成知识结构严重偏差,因而形成一批脆弱的民族脊梁。所以在国家大灾难来的时候,除了极少数像王阳明这样文武全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人物,绝大多数人物只有“文死谏,武死战”,束手无策,一死了之。《红楼梦》小说对此有讽刺,这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价值观和历史局限。绍兴官员也免不了。比如1645年清朝军队南下占领江南,明朝绍兴官员组织起钱塘江保卫战,但很快溃败;清军铁蹄踏进绍兴,明朝绍兴官员只好纷纷自尽而亡。临难有大节,是可贵的;遇事无办法,却也极为可悲。
①明代从普通成年知识分子变成进士,取得体面做官资格的综合录取率,是上述童试录取率5%、科考录取率12%,与乡试录取率3.33%、会试录取率10%(文徵明《甫田集》卷十七《送周君振之宰髙安叙》: “乡贡率三岁一举,合一省数郡之士,群数千人而试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得隽者曰举人。又合数省所举之士,群数千人而试之,拔其十之一,升其隽者曰进士”)。这四个比率的相乘,也就是0.002%,十万分之二!这还是较高的估计,因为乡试录取率还有更低的。如瞿景淳《瞿文懿公集》卷六《应天府乡试录序》载,“圣天子御极之三十有七年戊午秋,维大比之期,天下士挟策就试者所在云集,应天府府尹臣某……乃合提学御史臣某及六馆诸曹所选士五千有竒,三试之,昼夜翻阅,遵制额,拔士百三十五人”,可见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应天府的乡试,从5000多名科举秀才中录取举人135名,录取率只有2.7%。陈际泰《已吾集》卷一《贵州乡试录前序》又载,“己卯,贵州乡试之役……进提学臣龙文光所取士一千四百有奇,锁院三试之,得士三十七人”,可见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贵州乡试录取率只有2.64%。马世奇《澹宁居文集》卷四《江西乡试录序》更载:“我皇上御极十二年,岁己卯……进提学参议臣侯峒曾所遴士五千八百有奇,三试之,焚膏继晷,参伍毫芒,得士一百有三人。”5800多名科举秀才中,只录取了103名举人,录取率竟低至1.78%!
②明代六部尚书之上,还有殿阁大学士,一般人以为品级更高。但殿阁大学士虽备皇帝顾问,代拟圣旨,俨然宰相,但本身品级较低,只有正五品。
③崇祯十四年(1641),著名学者、时任苏松巡按的山阴祁彪佳鉴于饥荒蔓延全国,绍兴亦连年受困,作《救荒杂议》(《祁彪佳集》卷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6页)诸款,其中第一款就是建议绍兴官民节食,内云:“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即以山阴一县计之,田止六十二万馀亩,民庶之稠,何止一百二十四万。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可见明末绍兴府山阴县的人口就多达一百二十四万以上。
④李德甫:《明代人口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89页。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