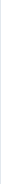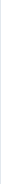摘 要:徐渭处在中国戏曲发展转型时期,传统方面他得之于宋元时期戏曲文化的滋养,地域方面又受惠于吴越文化的熏陶;越地的中心--—绍兴的水土民风孕育了徐渭身上特有的文化情结。其代表作《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不仅思想上富有积极意义,而且还独具地域方面的“南味”,本文拟通过《女状元辞凰得凤》的文本及文化分析,透视徐渭戏曲创作中的越文化情结。
明人徐渭不仅是一名创作风格特出的画家,还是一位影响力极大的剧作家。据学界考订,现存并确定为他所作的戏曲作品只有《四声猿》杂剧,另有理论专著《南词叙录》一本,但仅此二作,亦足以奠定其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四声猿》本身内容大胆,笔墨激扬,一展追求自由平等的别样情怀;另一方面,从整个明代看,《四声猿》的独创性也开明代戏曲之新风,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承载了作家的思想意绪,但作品中所传达出的作家思想精神源于何处很值得探讨。徐渭的创作与他本人的经历分不开,其所生长的越地文化,就对他有着诸多的重要影响。
《四声猿》包括四部戏曲,分别为《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以下简称《女状元》)。这四部作品,虽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但却共同展现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层面不可调和的悲剧意识。其中五折的《女状元》,全用南曲,其他三剧,并用北曲。徐渭实际上开创了以南曲作杂剧的新写法。全剧尽用南曲,吴梅先生称之为“南剧孳乳”。《女状元》是否当为南曲杂剧滥觞,尚待探究,但其文中处处透露出的越文化元素当是四剧中最为明显又深入的,笔者将以《女状元》中的越文化因素为阙口以探寻徐渭的精神世界。
“就越文化的实际来看,我们认为,将越文化的核心区划在以绍兴为中心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是比较妥当的。”[1]如果非要给越文化界定一个空间范围,那么就当是浙江地区了。自古以来,越中地区就以风景优美著称,其临海靠山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风景的多样性,李白、陆游等都曾作诗赞颂,李白曾说:“秀色不可名,青辉满江城。”陆游的《舟中作》曾道:“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风景秀丽不仅能怡情,更能激发人的创作灵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探讨过环境与创作的关系甚至举屈原创作为例:“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自然环境不能决定文人创作成果如何,但至少如画的江山景色给人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而生长在越中或生活在越中地区的人们,吸取山水自然的灵气必不会少。除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精神力量,越中地区悠久的人文精神也必然会给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带来更为丰富的体验。
越中文化最远可以追溯到大禹时期,《史记·夏本纪》中有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岁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因为将大禹葬在了越地,后越地得以被重视,单独封王成国,由是越地有了自己的政权,一方文化开始有了发展的根基,除了大禹带给越中民众以英雄主义气概之外,越王勾践卧薪藏胆的励志精神又赋予越地民众以大禹般刚强兼柔和。当初勾践不惜隐忍装傻,最后得以重振旗鼓咸鱼翻身。祖先们坚强不屈又隐忍有术的人格血脉在越中大地得以延传,就好比江南延绵的水,粉墙黛瓦,家尽枕河,没有一户不受感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儿女。越中地理和历史上的独特性注定其地域文化发展不再单调。
徐渭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就生活在越文化最初起源的地方,其诗词曲赋里的江南才情自是韵味十足,尤其是明初期,越地受阳明心学的影响较甚。徐渭影响最大的戏曲《四声猿》被称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2],而他本人也被评价为“奇人”,不仅“行奇、诗奇、文奇、画奇”[3],只要跟徐渭沾上边的事物或人,都笼罩上一层奇特的色彩。原因何在,徐渭为何如此之“奇”?笔者猜想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颇有关联。徐渭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以概括如下:
(一)风景秀丽激发创作热情。越中地区,山水风景怡人,如同一幅幅山水画作,又好像一片大的私家园林。遥看如今的越地风光,绍兴的流觞曲水,就可知生于斯长于斯的越中民众是怀有怎样的灵动深蕴气质。从人的成长来说,只有人的精神融入到自然景物中,人与自然景物风貌和谐相融才能达到人景合一的和谐生存状态。由此,在这样环境下生活的徐渭,不仅作诗有材,作画有物,作曲更是蕴育着越中地域之风神。
(二)历史感染影响创作心理。古越之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古有大禹勾践刚柔并济,后有阳明心学风起云涌。明初,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开始思想醒悟从而崛起。从前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已经压制不住人们想要正视自己,发展个人的要求。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的“心学”,将人之心存于天地之中,指出做人要有良知,但又不代表抹灭人的个性。随着这样的理论逐渐流行,徐渭也受益其中。在徐渭的《畸谱》中曾经记载了王阳明弟子的言行,文中无不透露出敬意,由此可见徐渭受其影响之深。正是由于受先驱与今人的影响,徐渭在其戏曲创作中不仅追求风格的本色,更乐于倾吐内在的心声。而王阳明也是越中人,乡贤的潜移默化也让徐渭身上多了一层心学的附着。
(三)戏曲传统悠久徐渭遵循潮流。戏曲这一文学形式,在越中地区发展较早,早在先秦时期,越人就善于歌舞。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曾对西施歌舞表演作有形象的描述“西施歌舞……扶旋猗那,弱如秋药”[4]。越人还大兴巫风,王国维曾述:“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5]唐时有参军戏,宋有南戏,直至明中期,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也在此兴起并流行各地。可见越中地区戏曲源远流长。在这样浓厚戏曲传统的熏陶下,徐渭创作戏曲的热情似不应见怪。
徐渭与越文化的关系深厚沉蕴,如同每一个越人一样,其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融入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而在作品中展现出的,应当是其精神深处和内心想要表达的一种物化行为。这里我们仅以其剧作《女状元》为例,来分析其中透露出的越文化情结。
《女状元辞凰得凤》是《四声猿》[6]中最晚作的一篇戏曲作品,题材是由徐渭好友王骥德提供,据说是王骥德向徐渭诉说了一个女扮男装考取功名的故事并向其推荐,于是是徐渭欣然接受这样一个素材,创作了《女状元》。但无论其故事叙述还是曲文唱词,处处都流露出徐渭的越文化情结,其本人情感寄托也表露无遗。
《女状元》描述的是女子春桃为摆脱贫困的生活,想借自己的才华考取功名获得利禄,遂女扮男装化名黄崇嘏前去赴考。这个黄崇嘏不仅会画能书,还善长抚琴赋诗,可谓才华横溢,不仅一举夺魁还名声大噪。后因丞相欲招其为婿,她才不得已说出自己是女子的事实,回归女儿身的黄崇嘏也最终回归家庭,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从此她的才华再无可能挥洒于庙堂之上,而只能在儿女情长之后伴之以终身柴米油盐的庸庸碌碌。这部作品中除却结尾稍显传统落后,前面的故事情节无不扣人心弦,激动人心。细看其内容,我们就能看出徐渭越文化情结处处彰显,成为影响故事走向的主要筋脉。
(一)女扮男装反映越女心思。在封建社会中,女子向来地位低下。且不说有没有如此才华,就是有,也不好擅作主张抛头露面。但春桃为了生活得更好,不仅计上心头想出主意,还果断立马行动。“我这般才学,若肯去应举,可管情不落空,却不唾手,就有一个官儿?既有了官,就有那官的俸禄,渐渐的积趱起来,么量着好作归隐之计。那时节就抽头回来,我与你两个依旧的同住着,却另有一种好过活处,不强似如今有一顿吃一顿,没一顿捱一顿么?”这样的行为乳母黄姑非常赞同。当下二人就换装进城,按计划行事圆自己的温饱梦去了。春桃为了生计,毅然决然走上了科举之路;她想依靠自身才学解决自身穷困,这就是去考科举的初衷。这样的读书带有极重的功利色彩和追名逐利的动机,与求学问道宗旨相背。
徐渭在戏曲中让女子主人公不再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而是思想独立、性格独立的具有先见意识的新型女性形象。这样人物的塑造,和徐渭越文化情结分不开。越中地区的人们本身思想开化,接触的新鲜事物也多,加之阳明心学的流行,女子自主性格加强,产生翻身做自家的主人的意念完全可能。徐渭带有这样的情结创作出来的人物,也是冲破一切传统束缚,跟从自己的内心,人生诸事由己做主,也正是这样,我们才看到了春桃化身黄崇嘏后的精彩表现。当最后真相大白之日,黄崇嘏敢作敢当,显示出自己的果断刚毅;终了也能欣然接受花好月圆的安排,体现她刚柔并济的一面。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然山水对人物的影响。黄氏对自己生活环境很满意:“且喜这所在涧谷幽深,林峦雅秀,森列于明窗净几之外,默助我拈毫弄管之神。既工书画琴棋,兼治描鸾刺绣”,明丽的山水滋润出女状元的锦心绣口,配合着她的才华横溢。徐渭将这些环境因素着意渲染,亦体现出“江山之助”对文人构撰艺术作品之作用。
(二)徐渭与南方之曲。剧中黄崇嘏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谙熟人世,断案准妙。一开始,考官就出一道乐府令考生当下完成。黄对的是“当一壶,赛真珠榨滴才,何事跑穿鞋?要引佳人笑口开,怕蹙损了远山眉黛。亏杀他跟着措大,走遍天涯,还消得领雉头裘,付酒家酬债。”后面其他考生再如何对,都不如黄崇嘏的妙,细心的读者也应该发现。黄对的乐府里明显有女儿家的细腻所在,若非身为女儿身,怎会如此懂得女儿心。再后面黄崇嘏体察民情,机智断案。全曲流利宛转,文采斐然。全戏采用南曲。虽南曲之兴未必就在此剧,但徐渭扬其当地戏曲之心可以让人接受,因为南曲的清丽柔约更适宜在戏曲中记叙故事。《女状元》在徐渭这是有着特别寓意的,前面说到它是四组剧中唯一的用南曲创作的。但是徐渭为何独独看中这部戏呢?徐渭又为何同意加上这出戏凑成《四声猿》的四部呢?这里即要涉及谈到徐渭的戏剧理论观。明代嘉靖年间徐渭写出《南词叙录》,堪为南曲理论的发端。成为了整个封建时代一本独一无二的南戏专著。其中他谈到:“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浙,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憔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纤徐绵吵,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7]徐渭站在比较中立的角度,从审美角度分析,指出北曲粗犷豪迈,多阳刚之气,南曲则轻柔婉转,有阴柔之美。徐渭这种切中肯綮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声猿》的艺术实验为大胆改造杂剧传统铺平了道路。结果,晚明出现的杂剧,多由南方人创作,混合了南方的曲调与韵律,与旧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8]可见其影响了南方创作家来创作南杂剧。这无疑是这位深受越文化影响的徐渭对南方戏曲,对越文化的反哺。所以《女状元》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徐渭为弘扬南曲,践行其戏曲理论的标准文本。在他眼中,春桃如同一个活生生的越女子,唱着南曲,富有个性,才气斐然,正代表着南方文化孕育下的才女形象。
(三)投影徐渭。黄崇嘏,实五代时前蜀邛崃(治所在今四川)人黄使君的女儿,故事本事最早记载于《太平广记·妖怪类》引《玉溪编事》。金元杂剧《春桃记》均敷衍黄崇嘏中状元之事,明代杨慎的笔记《杨升庵外传》亦记此事。在《太平广记》中黄崇嘏是“乡贡进士,年三十许”,可在此处徐渭将之改变成二十岁,相差十岁反而中了状元,并且是女扮男装,可见寄托了徐渭深深的个人情感。嘉靖十九年(1540)他20岁再次参加绍兴府童试,经过申请参加复试,录取为童生。但是接连八次科考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徐渭的二十岁,和黄崇嘏的二十岁起点略有相似,但是最终的结局天悬地隔。她实际就是另一个徐渭的投影,徐渭希望自己生逢其时,不要遭遇怀才不遇的厄运。付之于其笔下的女状元正是一个绝佳之理想人物。面对八次失败,《女状元》里面徐渭也借戏中人口吻发牢骚,“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这也是对当时科举绝望后的反思,也对科举科考官的百般嘲讽。
为什么徐渭如此重视科考呢?其实这种科举盛况,徐渭在戏剧中对科举的重视,都深深反映出明代江南考生包括越地区的科举情况。在当时,江南考生考取功名的热情和考中率远胜其它区域。江南不仅经济高度发展,对文化、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是其他地方难以望其项背的。清人称颂道:“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江南科举之胜有一原因就是,世家大族的重教风尚。徐渭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读书条件甚好,也是神童,可他连续八次科举失败,一方面表明其百折不挠不服输精神,一方面也反应了江南考生对科举的执着。这种江南文化的熏陶不得不令徐渭投身其中狠下功夫。同在绍兴府,贤圣王阳明弘治十二年考取进士,王阳明之父王华则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这些都是绍兴府之骄傲,也是越地科举人才之楷模。
但是未中举的徐渭,丝毫不能掩饰其在《女状元》过人之才赋。如第四出外末所说:“你云龙两物一身兼,孟郊怎受得昌黎拜?”后面黄崇嘏有言:“我崇嘏一向的遮掩呵,似‘折戟沉沙铁半销。’老师呵,你可该‘自将磨洗认前朝。’我呵,天元不曾许我做男子,这就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小姐,辜负了你,且‘铜雀春深锁二乔’。 第五出中净赞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不管是化用典故还是引用古诗词,都能符合人物身份,不觉掉书袋卖弄之嫌。作者和剧中人的学识才华皆深深吸引此剧的受众,这样的例子在《女状元》中比比皆是。徐渭在作品中表达出对科举考试的复杂态度,展示出自己点石成金的文艺修养,而这正是越地区越文化所浸润、钟毓的结果。
清初著名学者周亮工曾说:“青藤自言:书第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语耳。吾以为《四声猿》与竹草花卉俱无第二。”[9]周亮工这样的评价是有根据的。就徐渭一生成就而言,《四声猿》之地位毋庸置疑,而《女状元》又是其中尤其有特色的。
徐渭生于越地并死于斯,其一生落拓不羁,布衣秀才,饱受人世沧桑,虽间或有人生中的短暂得志,但总归未能尽施其才。但是他的书、画、诗、文等技艺才能确属当时首屈一指的。他深深扎根于越文化的大地,被家乡文化所吸引和并深深浸染其中,也因此造成他的作品中明显包孕有诸多越文化情结的因子。《女状元辞凰得凤》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作品寄托了徐渭的一生对于科考的百般凝结感慨,寄托了对世情人生的反思,表达了他的美好人生理想,他的多情才女女状元形象的塑造,不啻为他的理想社会的一则有力宣言。另外,全曲用南曲创作,如同他对南方戏文之曲的喜爱一样,践行着他《南词续录》中的戏曲理论观,尽显南曲柔婉之美,但又能做到辞不害意,文辞相合;戏剧的主人公黄崇嘏有着越地女子的刚柔相济的品性,其参加科举的初衷多少符合当时很多人的心态,而戏中所呈现的科考情形,也是当时江南科考之实际观照。
[1] 高利华,邹贤尧,渠晓云:《越文学艺术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曲研究院1980年版,第167页。
[3] 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2页。
[4] 张岱:《陶庵梦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5]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国戏曲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6] 本文所引用《四声猿》文本内容,均出自《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8]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7页。
[9] 周亮工:《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版,第2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