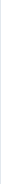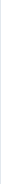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人与水之间的活动,就有了文明的律动。管子说:“水为万物本原”[①],这不仅仅是中国先哲的至理名言,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泰勒斯也曾提出过“水是万物的始基”[②]的著名命题。作为自然的元素的水,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明史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事实上也如此。世界上凡是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大都与江河水域有着渊源关系。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巴比伦文明。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孕育了北非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印度的古文明产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国的古代文明则与黄河、长江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也影响、制约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
越文化发生于长江下游,被视为长江文明的有机组成,它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从区域文化宏观研究角度,需要与长江文明联系起来考虑[③];若具体到越文化发生形成的历史背景,则须与越地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地理自然环境相维系了。无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越地的文明史总是与水的治理史息息相关。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绕不开关于谁的话题。一部越地文明史,从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如何与水环境共存并协调发展的历史。
古越先民生活在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一带,亚热带温暖的气候,充足的雨量,丘陵和平原交错的地理环境,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在史前的古越大地上,较早地绽露出人类文明的曙光。浦阳江流域、曹娥江流域、姚江流域和钱塘江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的先民在这里曾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这个地区不仅有着完善的史前文化遗址,如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曹娥江上游的小黄山遗址,浦阳江下游的跨湖桥遗址,姚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而且还创造了与环境相一致的地域文化特征。
从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人们发现亚洲最早的栽培稻遗存等实物,证实了长江下游地区的越地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上山遗址年代大约距今为约11000—9000年之间,年代相当古老,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④]
在萧山跨湖桥遗址,人们发现了古越先民8000多年以前舟船制造的技艺。[⑤]由于生活在频临江海湖泊的自然地理环境里,越人很早就发明了水上交通工具,舟船的制造和利用可说是古越先民最伟大的贡献。
余姚河姆渡遗址向人们展示了7000多年前古越先民开凿的水井、人工栽培稻以及水生动物(包括鲸、鲨)捕捞遗存。为了适应该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越人创造的全新的“干栏”式建筑样式,[⑥]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同类遗址。
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人们发现了许多植物的种子、农具和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可见当时农耕和手工业水平的提高。钱山漾和水田畈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船桨[⑦],反映了水上交通与渔业生产的进步。
在越文化的发祥地,伴随着众多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所提供的大量实物证据,表明彼时的古越先民生活在近海的平原地带,已较早地进入了农耕社会,并已建立起近万年的文化发展序列。从上山、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良渚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到马桥等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越地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是完整的,清晰的。
然而,在近万年的文化发展序列中,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越地曾一度发生了文化逆转,先进的良渚文化在越地突然消失。在夏、商、周整整三代的历史时期,越地的文化始终处于低迷状态,明显地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越地文化的突然逆转,现代环境科学研究和考古发现成果认为,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存在着一个全新世大暖期,中国东部有传说中历时数代的灾难性的大洪水可能导致良渚文化的结束。气候与环境研究方面的学者不仅认为中国远古历史上因全球的气候突变曾发生过大洪水,而且对洪水发生的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一致而明确的认识,即距今4000年前后。[⑧]
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进而以卷转虫海侵说解释越地文明的停滞和延缓,认为卷转虫海侵的过程,是越地自然环境恶化的过程。[⑨]在第四纪最后一次海侵即卷转虫海侵以前,于越民族早期居住的是一片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近海平原。但在海侵的过程中,这里沦为一片浅海,越族开始流散。于越民族在会稽山地渡过了几千年的迁徙农业和狩猎业的生活。及至海退以后,于越族繁衍生息的这块肥美平原已经成为一片沮洳泥泞的沼泽地。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这里潮汐出没,土地斥卤。要把这片可怕的盐碱沼泽地改造过来,将是一项多么艰苦卓绝的工程!鉴此,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于越地的大禹治水的传说,其实是卷转虫海侵淹没东部沿海平原,然后随着海退的过程及其越族人民胼手胝足,改造这种恶化了的自然能环境而使东部沿海平原再度露出海面这一自然—人文过程在越族人民头脑中的曲折反映。[⑩]
大禹治水神话广泛流传,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愿望。至于大禹治水成功的结果,则是海退以后,自然环境有所好转的客观反映。在这个过程这中,于越部族建立起来的越国,谱写的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是值得关注的。
卷转虫海侵以后,一个已经在沿海平原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生产经验和原始文化的于越部族,从平原倒退到山区,进入森林密布、地形崎岖的会稽山地,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11]生活。于此同时,在中原地带随着部族联盟的崛起,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捷足先登,首先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在新石器时代曾经创造过璀璨文明的古越部族,直到西周时期,他们的身影才偶尔出现在中原文明的舞台上。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11世纪):“于越来宾”。此后又是漫长的岑寂,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越部族涌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越王句践,越部族才正式开始跻身于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粗线条地爬梳一下先秦时期越地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令人惊心动魄的不仅仅是于越部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越国演绎的称霸历史。在越部族赖以生存繁衍的这片土地上,一千多年间发生的自然环境沧海桑田的巨变,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于越部族生活的环境,北部是一片潮汐直薄、泥泞不堪的湖沼平原,南部山区则“山林幽冥”,是一片虎豹出没、林木茂密的原始森林,开发及其艰难。《管子·水地篇》在评价越国的水土与人民是就说:“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意思是说:越国的沿海平原都浸泡(洎)在混浊的水中,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肮脏、愚昧而且多生疾病。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越人生活的水环境是多么地糟糕不堪!是勤劳勇敢的越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畏艰辛,胼手胝足修筑海塘,建立聚落,改造环境,一步步地把越国的都城从山地都城(嶕岘)、山间盆地都城(埤中)、山麓冲积扇都城(平阳)迁徙到平原孤丘都城(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12]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到了越王句践时代,终于将因卷转虫海侵等原因变为一片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改造成能够安家立国、称霸一方的根据地。
自然环境是历史演进的舞台,也是演绎文明的必要前提,自然环境的变迁直接影响到文明的进程。一些学者则明确指出了中国文明形成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特殊关系,认为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13](吕思勉《中国民族史》认为夷与越是同一民族,淮北称夷,江南称越)但是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却是环境因素起了关键作用。这至少表明在早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对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不少研究者显然注意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联系,因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自然环境变迁对人文历史演替的各种影响。
越国从初霸、兴起到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春秋五霸之一而专制东方近百年的辉煌显赫,从被楚国所大败而衰落到最终被秦所灭亡的曲折而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珍贵的范本。这个范本所演绎的,不仅仅是人文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的变迁推动和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迁,而自然环境的变迁也曾对人文的发展变化起过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如海侵海退等大自然的剧变对人文的影响)。[14]
自然环境的变化给人文历史留下了特殊的印记,这就是地域文化在形成之初自然环境对人文发展的作用。
在农耕社会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整个山会平原的再次开发,可以说是古代水利建设的产物。句践三年(前494),越国兵败退居会稽,范蠡修建南池、坡塘,开我国内塘养鱼之先河;越国开凿山阴故水道,以连接都城与战略后方,开挖出的土方,北建山阴故陆道,南建富中大塘;围堤筑塘,改造沼泽平原。越国对堤塘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迅速造就了一批农业生产基地,为山会平原的广大沼泽地的利用创造了条件,既奠定了越国中兴和争霸的基础,也为东汉的鉴湖工程的实施打下了基础。
东汉时期会稽郡太守马臻发动民众修筑的鉴湖,是历史时期宁绍平原上一个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承前启后,在越地文明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古鉴湖是在句践时期的“富中大塘”和“吴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的一个系统的水利工程。它以会稽郡为中心,东至曹娥江,西抵钱清西小江,水源范围面积约为1200平方公里水利工程。据孔令符《会稽记》载:“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指的是其拦洪排灌和拒咸蓄淡能力。鉴湖水系比较复杂,会稽山脉绵延100公里,山脉丘陵分布和走向十分复杂,古代鉴湖号称有三十六源[15],会稽山脉的复杂地形和源头众多水系为古鉴湖形成直接提供了丰富的水源。鉴湖与周边的浦阳、曹娥两江以及钱塘江下流江道构成了复杂的连带关系。古鉴湖又处于依山濒海特殊的地理区位,在历史时期,由于海塘和江塘均为修筑,钱江大潮由曹娥、浦阳二江倒灌而入于鉴湖水系诸河,加上二江(特别是浦阳江)在历史上的频繁洪水,常常造成山会平原因海潮倒灌、山洪泛滥引起的严重内涝,平原北部的沼泽地成为一片斥卤泽国。这就是古代鉴湖地区庞大的水系范围和时时面临的洪水危害。
越王句践时期,人们对水环境的适应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人们有意识地筑堤围湖,向水争田。越国修筑的富中大塘、练塘等水利设施,旨在调整山会平原的水面和地面的比例,发展农业生产。到了汉代,由于湖泊群已随海岸线走向北部平原,山会平原水面和地面的比例明显有所改观。平原南部的湖泊大半淤积,平原中部的湖泊虽然形成不久,但也开始走向湮塞,使土地面积大幅度增加,超过了水面。在鉴湖修筑之前,人们在会稽山麓冲积扇筑堤围湖,如春秋末期的吴塘、苦竹塘、坡塘、南池,东汉时的回涌湖,这些都是用来蓄淡灌溉人工湖泊的雏形。
鉴湖水利工程,是这一地区人、地、水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这一地区的水地比例一直失调,水多于地,因此人们对水地关系的调整往往是削水增田。到了汉代,在已经开垦的地区,已有水面积不足之虞,而鉴湖工程的根本目的是拒咸蓄淡,是舍田增水,改善近海的沼泽平原,增加山会平原的淡水面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保持水地之间的平衡性。
经过东汉以后持续的水土改造和根治,逮至两晋时期,鉴湖的经济效益开始得以全方位体现。晋永嘉以后,这里已是一片安宁肥沃的乐土,以王、谢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纷纷南迁,他们带领部曲、私附近入宁绍平原,把庄园、别墅安置到会稽一带,客观上促进了会稽郡社会经济的发展。贺循开凿西陵运河(浙东运河)是继马臻修筑鉴湖后水利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水利和航运两方面对越地经济和社会产生促进作用。它沟通了东晋政权京都建业和会稽之间的联系。六朝时期,越地人口增长加快了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使该地区农业生产由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的转变,物产变得更加繁富。鉴湖除了灌溉农田之功能外,湖面淡水栽植和养殖业也发展起来了,茭、荷、菱、芡之实不可胜用,鱼、鳖、虾、蟹之类不可胜食[16],以至于“今之会稽”犹如“昔之关中”[17],自然环境有了根本改变。到了刘宋之时,史称会稽郡“带湖傍海,良畴亦数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18]一郡丰收,三吴不饥,水利为农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会稽郡已经成为东南一带著名的粮仓。
到了唐代,鉴湖外筑海塘,内建斗门塘闸,又与郡城(罗城)内河水道融为一体,水利系统渐趋完善,唐代鉴湖由于海塘的修筑和玉山斗门的建造,内外堤塘形成一个系统。“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19]既可防洪,亦可抗旱,还带来航运、水产一系列综合效益,鉴湖于是进入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当时的越州不但经济繁荣,人口众多,而且文化鼎盛。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农桑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20];江南安定,水土资源优裕,经济发展较快,全国经济中心从北方移到江南。越州人口增达50万之多[21],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都很发达。“越之有鉴湖,如人之有肠胃”[22],鉴湖的水利调节功能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逮至唐代中后期,由于南部山丘三十六源水土长期流失等自然因素,鉴湖周边的淤浅处已出现葑田现象,水域的范围开始缩小。为了保证灌溉,保持水土之间的平衡,周边地区开始兴修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如夏盖湖等,试图在局部上缓解鉴湖淤积而引起的淡水资源短缺的压力,但水地之间的矛盾已经显露。
入宋以后,由于人口密集,耕地不足,人们对于土地需求量也成倍增加。鉴湖由于泥沙淤积,湖底逐渐增高,湖周的淤浅处干洄出大片肥沃的土地,很自然地成为人们争相围垦的对象。靖康之乱以后,南宋王朝定都临安,越州成为京畿地区,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围湖垦田现象愈演愈烈,此事虽然曾经在朝野引发过多次有关浚湖和废湖的争议,但鉴湖的湮废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至宋孝宗乾道初,鉴湖除特别低洼处潴成新的湖泊和积水河道外,传说中八百里湖已基本垦为农田,鉴湖原来拥有的水利调节功能逐渐被北面的海塘和闸堰所取代。宋以后鉴湖的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鉴湖留给后人的已不是水利调节之功,取而代之的则是舟行水运之便和田畴河网交织的水乡风光。
鉴湖开发虽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湖成之后,给越地的发展带来的契机却是无穷的。南宋之前,鉴湖外拒海潮倒灌,内为蓄水之腹,灌浇良田9000余顷,从东汉到南宋,鉴湖工程效益至少持续了八个世纪。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发挥了拒咸、滞洪、灌溉等多重水利功用。古鉴湖的建成使山会平原北部的沼泽地得到了大面积的改造,使其从整体上由“荒服之地”向“鱼米之乡”过渡成为可能;鉴湖水系的持续开发利用,使山会平原摆脱了恶劣的织染环境,变成了河湖交错、良田沃衍的富庶之地,并且在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同时,最终实现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23]鉴湖水系的形成和开发利用恰恰印证了文明史的一般规律。
现有的文献资料都证明,在古鉴湖形成之前,越地是一处自然环境及其恶劣,被认为是不宜生存的地方。春秋时代,管仲视越地为穷山恶水[24],《庄子·杂篇·天下》云:“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越王句践说:“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25],都说越地沼泽遍布,低下潮湿,在这里生活的人愚昧落后,生活困难,寿命很短。清人李镜燧在描述越中地貌来历时也说:“越中地属海隅,南至山,北临海。地势南高而北下,江流溪源下注,海潮怒激,江与海相通,吐纳无节,本天然一泽国耳”。[26]越人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样的水环境中,避开水患,谋求生存乃是安生立命的第一要义。为了生存首先必须适应这个环境,继而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改善环境。在文献记载中确也有不少越人与水斗争的记载,如《越绝书》卷四载:“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越人“善海”习水[27],最早发明了舟船进行航海;为了避潮湿,越人发明了的干栏式建筑。有史以来,越人为谋求生存和发展,利用自然,改造环境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抗争无疑是有意识的,是带着明确的现实功利目的的。人们疏浚河流,修筑海塘是为了平息水患,安居乐业;拒咸蓄淡,开垦良田是为了农业丰产,实现因劳动而得到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回报。然而,越人在治水问题上脚踏实地的努力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看来不仅仅只是物质利益和经济发展的回报,他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特色显著的区域文化——越文化。这就是六朝以后人们为什么多以审美的、文化的视觉来看待鉴湖的原因。
马臻发动民众修筑鉴湖之初,鉴湖充其量只是宁绍平原上一个解决水患和生计问题的水利工程。但恰恰是鉴湖的形成,才从根本上改造了整个鉴湖水系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极大地优化和美化了流域地区的水土资源和自然风光,从而吸引了许多北来南迁的大族在会稽安家定居,经营发展。东晋南朝,中原衣冠荟萃于越,南北大族已在鉴湖地区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促进了越地经济与文化。东晋南迁士族带来的闲淡风度与会稽山、鉴湖地区的自然风光的融合,大大启发了六朝人对会稽风物的灵感关照,使越中山水逐渐走入了文学艺术的审美视野,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被后人推赏。
鉴湖水利对塑造越地环境,孕育山川灵秀,培育斯文之风确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据《世说新语》注引《会稽郡记》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风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经过东汉以来长期水土根治,会稽一带的自然景色已经十分宜人,从客观上迎合了士大夫文人追求人生自由和崇尚玄学的审美趣味。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往往使人应接不暇。稽山鉴水一旦进入士大夫文人视野,马上就成为他们生活中无法分割的情趣和牵念。六朝人比欧洲要早一千多年发现山川林野的审美价值,并形成了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世说新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28]画家顾恺之赏叹会稽山川形胜的话,一时传为美谈。永和九年王羲之等社会名流在鉴湖之畔的兰亭雅集,曲水流觞,诗酒风流,在山水中悟道,成为千古韵事。越地自然风物还滋润着“二王”的书风,书法创作于是在越地蔚然成风。谢灵运以会稽、永嘉的山水胜景入诗,从此山水描摹成为南朝诗人笔下最常见的一种题材,这对中国山水文学最早在越地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会稽秀丽的山水,也为僧人的传教和悟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般若学的各个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都钟情于越中自然山水,从东晋到南朝的一百余年间,会稽境内高僧云集,很快成为中国南方的佛学中心之一,对隋唐时期天台宗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水文化是审美的文化,水的柔和灵动、壮阔虚幻,诱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丰富了人们对美的感受,激活了人类形象思维的绚丽璀璨。六朝士人与自然融合无间使东晋南朝时期的会稽名扬天下,文风特盛,地灵而人杰,他们在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成就卓越,并直接延续到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随着中国文化的核心圈向南转移的一个重要时期。唐代安史之乱、五代吴越国和宋代靖康之变促使了中国整个经济文化中心格局的变化。唐时鉴湖水利系统完善后,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备。越地佛寺、道观林立,市井繁华,加上以鉴湖为中心浙东山水风光,引发了唐代士大夫对六朝士人文化踪迹的无限向往。李白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29]杜甫说:“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30]在中国诗歌发展最鼎盛时期,因追慕六朝士人的流风余韵,在浙东这方热土上居然形成了一条以自然、人文山水为特色的神奇的唐诗之路,吸引了400多位成名诗人纷至沓来,歌咏联唱,越州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之邦。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以鉴湖为纽带的浙东唐诗之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唐人创作中时时洋溢着的山水情结相比,宋人在越地似乎更喜欢营造浓浓的人文氛围。在“江浙人文薮”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京畿地区的越地,各路文化精英荟萃,名人辈出,日益呈现出泱泱大观的文化气象。陆游曾说:“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31]宋代的越地又面临着一次大规模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显示出管领风骚的地位。越地是全国最早刊印书籍地区之一,也是刻书业最兴盛地区之一。越地藏书名闻天下,南宋仅会稽一地就出现了左丞陆氏(陆宰)、尚书石氏(石邦哲)、进士诸葛氏(诸葛形仁)三位著名藏书家,耕读传家之风十分浓厚,即便在讨论鉴湖的兴废问题上往往也能综观历史,着眼于国计民生,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气度,体现出深厚的文化积淀。自六朝以来发展到唐宋,越地自然环境的改变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打造着属于这个地域的文化底蕴。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本身,从而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而具特色。
一个地域文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总是与其早期的生活环境分不开的。所以远取诸物,近取诸譬,在参证现实物质世界的基础上领悟并抽象出来的思维往往是最具有个性色彩的。古人云:“山以水为血脉,以草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32]水为越地带来了良好的国土资源、经济实力和独特的文化内涵。鉴湖水系就如越地的血脉,不但滋养优化了越地的自然环境,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通了越地的经济文化兴旺的脉络,促发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遵循着人类“适者生存”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因物质文明带来的地域文化面貌的根本改变。
鉴湖(镜湖)妙造自然,长期以来为后代孕育了一个“卓然天成”的山水空间,人文佳境。千百年来鉴湖从自然之湖、人为之湖到人文之湖,我们认为,鉴湖工程的人文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千百年来越地人民“缵禹之绪”,改造自然,最后成功地塑造地域文化品牌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鉴湖既是历史时期越地的“水利之父”,更是孕育越地文明、营造人文气象,遗泽后世的“母亲湖”。
鉴湖是我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尽管古代文献对鉴湖有不少记载,但主要集中在地理志方面的单纯的山川地理记述。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古代鉴湖进行研究,是从陈桥驿先生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对古文献进行认真分析并且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古代鉴湖在中国水利史上的重要地位得以确认。后来在绍兴召开的纪念鉴湖1850周年暨绍兴平原古代水利研讨会,标志着对鉴湖研究的全面铺开。此后,盛鸿郎先生、邱志荣先生等一批学者先后出版了《鉴水流长》、《绍兴水文化》等一批专著[33],把古代鉴湖和绍兴平原水利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古鉴湖研究,也引起了海外学者关注。日本学者有关古鉴湖的研究始于50年代,关注点在古代鉴湖的变迁和水利灌溉的关系,大阪大学的斯波义信对于古代鉴湖和水利史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34]一书中。耶鲁大学柯慎思(J·H·Cole)出版的专著《绍兴:19世纪中国的竞争与合作》[35]和瓦尔巴莱索大学的萧邦齐(R·K·Schoppa)出版的专著《湘湖——9个世纪的中国世事》[36]里也有对古鉴湖深入探讨。
总之,历史地理学界对鉴湖的认识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水利工程的地位和作用等加以考察论证,与越地文明历程和区域文化的演变往往缺乏必要的关联。水环境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变迁影响到人类社会、文化的演变,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37]水环境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的形成及发展中,地理环境通过影响人类活动而对文化施加影响,人类总是在自己直接所处的地理环境内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即通常所说的地域文化。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影响在以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对文明史的叙述要么着眼于历史的发展,要么着眼于地理环境演变,而缺乏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联系进行综合探讨。
鉴湖的水利与越地文明的依存关系和其发展演变转型的过程耐人寻味,恰恰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个案具有典型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我们题试图转换视角,从水利与文化的角度切入,通过考察鉴湖生成后生态环紧的改变所引起的人文环境的根本变化,以追寻鉴湖水利与地域文明之间的种种联系。重点研究在鉴湖形成前后的几个世纪中,山会平原如何从原来的沼泽连绵、土地斥卤的穷僻之地,改造成湖泊棋布、土地沃衍的鱼米之乡;变上古以来民风强悍、轻死锐兵的蛮夷之地,为文风鼎盛、名人荟萃、经济发达的文化之邦。力图从水患到水利的演变过程历史中,寻绎出越地人民在水的治理过程中不断推动的文明进程所谱写的精彩的文化篇章。
[①]《管子·水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李学勤、江林昌《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地位以及对东亚历史文化的影响》,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蒋乐平、郑建民等:《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金毅:《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一万年前的栽培稻》,《钱江晚报》2005年1月21日。
[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跨湖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⑥]1973年,在浙江杭州湾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这种“干栏”式建筑的遗址。据《考古学报》1978年第一期发表的浙江省文管会、博物馆有关《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
[⑦]《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二期。
[⑧]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中国文物》2004年第一期。
[⑨]陈桥驿:《于越历时概论》,《浙江学刊》1984年第二期。
[⑩]徐建春:《越国的自然环境变迁与人文事物演替》,《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11]《吴越春秋》卷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徐建春:《越国的自然环境变迁与人文事物演替》,《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13]王青:《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东方文明之光》第291页~29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王润涛:《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姚义斌:《洪水传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
[14]徐建春:《越国的自然环境变迁与人文事物演替》,《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15](宋)王十朋:《鉴湖说》上篇,《王文忠公全集》第七卷。
[17]《晋书》卷七十七《诸葛恢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41页。
[18]《宋书》卷五十四《孔令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2页。
[21]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8页,表二:南方诸州隋唐时户数及其升降。
[23]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曹葆华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08页。
[24]《管子·水地》第三十九:“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25]《越绝书》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6](清)李镜燧:《越中山脉水利形势记》,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
[27]《韩非子》难势第四十云:“夫待越人之善海者以救中国之溺人。”
[28]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29]《梦游天姥吟留别》,《会稽掇英总集》卷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60页。
[30]《壮游》,《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188页。
[33]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出版,邱志荣:《鉴水流长》,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盛鸿郎:《绍兴水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34]《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绍兴:19世纪中国的竞争与合作》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6]《湘湖——9个世纪的中国世事》,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7]韩宝平等:《水环境变迁对社会、文化演变的影响——典型实例简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