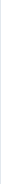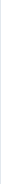中国哲学史上,历来都有为道与为学、传道与传经的区别。学界一般认为,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正式提出“道统”一词,从而最终确立了中国文化史中影响深远的“道统”观念。对于“道统”、“学统”之探讨,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积累了不少学术成果。像柳亚子[①]、熊十力[②]从读经角度,钱穆[③]、贺麟[④]从学术与政治之关系,张东荪从文明与文化的区分角度[⑤],进行了这方面的研讨。牟宗三则视科学为“学统”、德性之学为“道统”[⑥],还认为“自明朝一亡,乾嘉学问形成以后,中国学统便断绝了”[⑦],将“学统”又视为学脉而近于形上体悟和生命承担的“道统”,从而赞扬熊十力“复活了中国的学脉”,重开了“内在中心的体证”之门。另处,唐君毅、余英时、刘述先等也有相关辨析。[⑧]各位前贤时彦的论述,各有所侧重,本文打算顺着道、学二统相互融通的这一思路,“泛化”地采用他们有关“学统”的界定,认为所谓“学统”观念,主要指涉学术承担、学脉传承、学术精神,这种“学统”观念往往最突出地彰显于时代的大变局中。由此思想理路,我们来重新审视明清之际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以黄宗羲为中心,探析该时代对重建学统的要求及思想家对重建学统的努力。
我们谨持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认为明清之际的学术出现了新的转向,从思想转进的内在理路上看,表现为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轨。[⑨]这种转向的表现之一,即是明清之际的大儒们重建学统的努力。在“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产生了像黄宗羲这样的冲破时代“囚缚”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批判深入到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并从科举“时艺”中走出来,返求之六经,认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要复兴六经之学作为“大经大法”,并以“适于用”、“切于民生日用”为去取标准。黄宗羲重建儒学的品格,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之学,主张“通今致用”、“学贵适用”,反对科举之学、口耳之学,摒斥“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他主张道在六经,其复兴古代六艺之学及其多元人才观的表现之一,是他对“绝学”的提倡。他重视“学脉”,重视学校对世态人心的塑造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主张“学之盛衰,关乎师友”,力倡“自得”精神与学术争鸣。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重视主体性重建的务实、平等的近代特色。下面,我们将从黄宗羲的终极关怀等层面入手,多方面探论黄宗羲的学统观。
儒学的品格自来被界定为积极入世、经世致用、内圣外王并重、可以安身立命等,所以“儒学”并不等于后来出现的“科举之学”,尤其不等于“八股文”拘执士习学风而出现的时文之学、俗儒之学、批尾之学。所以,黄宗羲学统重建的努力,首先表现在他对儒学品格的重新赋予上。黄宗羲要人摒弃章句,反对以一科名为“究竟”,呼吁学术要“通今致用”,提倡“绝学”。这标志着新的学风之转捩的出现与初步完成,说明了在“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士人为学的精神追求,已基本上从几乎完全着重于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建构,转向了经世实学。
黄宗羲的这一致思取向,首先借资于陆王心学传统对“道”的体认,对“学”之“公共性”品格的赞同,以及对“道”与“学”之关系的认定。比如王阳明就曾指出“学乃天下之公学”:“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⑩]“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之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⑪]而此前的陆九渊早就认同“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圣人之学即“不容私”之公学,他说:“理乃天下之理,心乃天下之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不容私而已。”[⑫]明清之际的大儒刘宗周也指出:“夫道者,天下之达道,而言道之言,亦天下之公言也。”[⑬]
黄宗羲“承蕺山之绪”,整合理学与心学,对求“道”的百家之学作了赞扬,指出:“道非一家之私,圣贤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与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⑭]在黄宗羲看来,“道”由公学、公言,必然发为公用即“事功”。故而儒学的学术精神,必将经由儒者“立志”为“豪杰”而开显昭著,儒学的终极承担,就表现为百家发明“道”的体与用,立志于学道而“建功立业”。“道”虽为“一本”,但豪杰之士的求道过程,则表现为“求之愈艰,得之愈真”,而且表现在修身、创作、事功名节等各个领域。黄宗羲说:“道一而已,修于身则为道德,形于言则为艺文,见于用则为事功名节。”[⑮]为学求道能否“修于身”、“形于言”、“见于用”,还必须靠“立志”为“豪杰”而“求之愈艰”:
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凡民之后兴者,草上之风必偃耳。吾因而有慨,如洛、闽大儒之门下,碌碌无所表见,仅以问答传注,依样葫芦,依大儒以成名者,是皆凡民之类也。[⑯]
“ 凡民”指恪守程朱理学规范、缺乏远大的志向、在学问上毫无创见之人,他们“依样葫芦”、“依大儒成名”,“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身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⑰],徒有“阔论”,“当报国之日”而无益于解“大夫之忧”。这种空疏之病,导致世道“潦倒泥腐”,造成一种儒学无用的假象,“遂使尚论者以为建功立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这使得黄宗羲尤其深为忧虑!
黄宗羲对儒学品格作了重新赋予,认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要由豪杰之士来承担,他呼吁豪杰之士树立为国家与民族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全面发扬儒学治世的品格。黄宗羲以“经纬天地”、“建功立业”为理想人格的应有品性,就使黄宗羲的人格学说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跃动着功利主义”,但“它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功利主义”。[⑱]黄宗羲所赞扬的是学道与事功的合一。他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之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⑲]他主张儒学要既有益于修身,又要能“适于用”,在关键时刻能“救国家之急难”。对于明末学风的空疏,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批评到:“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性[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⑳]对此,黄宗羲也是深有感触,他认为儒学精神就在于去激发儒者强烈的责任感,应弘扬“扶危定倾之心”,挽救国家与民族的急难:
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贤指为血路也。[21]
黄宗羲只所以有此一番宏论,同他在抗清中虽“身濒十死不言危”、亲历“亡国之惨”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在《怪说》一文中叙述其抗清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生死遭遇时说:“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22]黄宗羲批判没有“扶危定倾之心”的“凡民”、“常人”、“庸人”与“乡愿”,痛斥他们“揣摩世态,陪奉人情”,“天崩地坼,无落吾事”。[23]
二、“科举之学,锢人性命”──黄宗羲对科举之学的批评
求道与问学之间的关系,为历来的哲学家所关注并在一定的问题意识刺激下予以求解。宋明理学强调“道”的一本性,与宰制性的“理”相通。到了明清之际,更多的是强调“道”展开过程的“万殊”性,即强调哲学家求道体验的个人性。在黄宗羲看来,“道无定体”,就不应“执一以为道”,而应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学贵适用”,学道与事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黄宗羲看来,儒者之学具有公共性的品格与达用治世的内在要求,而现实中是“科举之学”的流弊造成了“学道”与“事功”的分途,士人固守章句,不问究竟,悖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品格,所以黄宗羲对这种“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给予了激烈的批评。他说:
慼慼章句,锢人性命;视一科名,以为究竟。正如海师,针经错乱;妄认鱼背,指曰洲岸。[24]
黄宗羲指出,“今之人执一以为道”,科举考试只是“限以一先生之言”,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括帖”“四书”而不讲求实用实学,科举之学最终败坏心术、败坏人才、败坏儒学,遏制学术生机与学者之创新,造成“近来学人少,谁何识真伪。遂以科举学,劫人之听视。括帖上下文,原无真实义。推之入理窟,涂车可略地。有明三百年,人物多憔悴。”[25]考试并无“真实义”,到处是“理窟”,不识真伪的“近来学人”,只知“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地烦琐推理。这种过于精细的学思取向,直弄到“涂车可略地”,而仍视听不明,“有明三百年,人物多憔悴”,乃是科举害人不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这确为貌似丰富而实虚假的“学术泡沫”,是学术上的“虚假繁荣”。对此,顾炎武则批评较多:“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26]其实就是“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27]。
黄宗羲说“举业盛而圣学亡”[28]。举业成为一条不归途,“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这就造成“一定之说”横行,“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期可毕也”[29]。不知学问究为何物,不“深求其故”,以科举本身为学问目的,这样,“自科举之学盛,世不复知有书矣。六经、子、史,亦以为冬华之桃李,不适于用。先儒谓传注之学兴,蔓词衍说,为经之害,愈降愈下。传注再变为时文,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剿袭之中,空华臭腐,人才闒葺,至于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栋,而先王之大经大法,兵、农、礼、乐,下至九流六艺,切于民生日用者,荡为荒烟野草”[30]。沉迷于“时文”,不求自得于心,徒事讲谈,无用于世事,黄宗羲认为“自科举之学兴,士人以华藻给口耳之求,无当于国家之缓急”[31]。他指斥当时学界的学风空疏蹈虚:
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32]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强调“深造自得”[33],到了明代中叶,王阳明更是如此。他认为,当时世人皆扬言宗孔孟而贱杨墨摈释老,其实皆为学无所得,他质问:“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其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静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就从其有“自得”而言,它们甚至比那些“伪为圣人之道”者更有价值而更其可取。因此,阳明总结说:“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34]
《明儒学案发凡》中提到胡季随从学朱熹,朱子使读《孟子》。他日,朱子问季随:“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季随以所见来解释,晦翁以为非,说他读书“卤莽不思”。后来,“季随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其实,朱子也强调读书不要盲信,“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35],“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36]。朱子还曾说过:“学者不可只管从前所见,须除了方有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37]黄宗羲对朱子的创见并不隐讳,他说:“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38]与汉儒重文字、名物的考订与训诂不同,二程转向义理的阐发,并“自家体贴”出了“天理”二字;作为二程四传弟子的朱子,不拘成说,不泥师承,推扬“自得”与“新意”。黄宗羲认为,古人之于学者,其不如此“轻授”,如释氏一样最忌“道破”,是想让从学者“作切实工夫”,不要“作光影玩弄”,那只是“徒增见解”而已,关键是要有“自得”之见。学贵有自得之见,应摒弃泥古不化、固守章句注疏,对朱子学应活用,而不是将其作为科举场屋的工具。
“科举之学”末流之弊“锢人性命”,甚至导致国家败亡、文化沦丧,欲救学术流弊,在黄宗羲看来,应该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恢复科举应有的积极意义,改革用人制度,重新确立人才观,故尔,他主张复兴“绝学”,提倡多元人才观。
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看,“绝学”字面义为中断失传之学,实际上可绎解为:(1)孔、颜、曾、思、孟殁而不传的圣贤之学之统称,如张载所愿“继”的“往圣之绝学”,王阳明所言的“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39];(2)专指作为“六艺”原始意义之一的学问,用现代学术术语可称之为古代的科学技术。
我们通过阅读《黄宗羲全集》,发现黄宗羲曾多次提及绝学问题,如在《易学象数论序》中说:“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40]他在《答范国雯问喻春山律历》中说,范国雯给他看的楚郴的《喻春山书》,夸大言辞,自来儒者无不讥弹,而春山“自以律历为绝学,谓帝王历数真传”[41]。分别视象数与律历为“绝学”。在《叙陈言扬勾股述》中指出勾股之学失传而成为绝学:“勾股之学,其精为容圆、测圆、割圆,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42]其实数学“特六艺中一事,先王之道,其久而不归者,复何限哉”[43]!六艺之学中的精华,失传不归的不仅仅是勾股之学。他的学生万斯大,以考证方法研究礼经而著《学礼质疑》等书,黄宗羲在序中称赞他“锐志经学,六经皆有排纂,于三礼则条其大节目,前人所聚讼者,甲乙证据,摧牙折角,轩豁呈露,昌黎所谓及其时而进退揖让于其间者也。此在当时,固人人所知者,于今则为绝学矣”[44]礼学在后来必须经反复疏证,才能让人部分地理解过去的历史文化情景,而礼学的真实内涵大部分已经不可弥补的失传了。
黄宗羲对“绝学”叙述最为详尽的,是在《明夷待访录》的《取士下》篇中所说:“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之上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45]在该著《学校》篇中,他还主张各类学校除设五经师外,还要增设“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以便传授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举荐“绝学”人才,拓宽人才选拔途径,重视科技人才,这是黄宗羲所大力提倡的多元化的人才观,体现了他对人才“宽取严用”的取士原则。黄宗羲还有其他较宽的取士之法,如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郡邑佐、辟召、绝学、上书等等,这种人才观有助于部分改良原来科举一途因“取士而锢士”的弊端。“黄宗羲提出了要重视被科举制度排斥的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对那些精通科技的人才,也要选拔重用”[46],这确是值得注意的。
黄宗羲还分析了这些学问之所以成为“绝学”的原因。他在《周云渊先生传》中介绍了他个人的经历,他看到嘉靖间诸老先生文集,很少有人谈到周云渊的学问,像汤显祖给周云渊的信中谈到了,可惜并不知道究竟,周的同学唐顺之“其与人论历,皆得之述学,而亦未尝言其所得之自,岂身任绝学,不欲使人参之耶”[47]?对于历学,很少有较为稳定、持续的师承,以保证其为世人所关心、所学习、所发展,终成“屠龙之技”而失传:“余昔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及至学成,屠龙之伎[技],不但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48]说明这门让人“痴绝”的学问,是因为“不但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而失传。陆九渊也曾指出,这样“精微”的学问,不易得到“有绝识”的人才来传:“若夫天文、地理、象数之精微,非有绝识,加以积学,未易言也。”[49]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学、算学、兵法、医学等等,都有很多不容忽视的精华,并不是“无所用”的“屠龙之技”,黄宗羲这样说,是无可奈何的解嘲罢了。在当时浅薄的士人眼里,这样的学问无益于求取科举功名,故被人弃置不问。这是尤其令人痛心的!
黄宗羲提倡复兴“绝学”,也是“对当时流行的重德轻智、重道轻技的道德蒙昧主义的有力抗议”[50],“包含有人应该全面发展的思想”[51]。因为在朱熹看来,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从而轻视“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的知识。陆九渊则认为德愚夫愚妇可与知能行的“仁义忠信”,“学者之事当以此为根本”[52],德行与六艺的关系,是尊卑、上下、先后的关系,“仁义忠信”这些“德行事”,“为尊为贵,为上为先”,礼乐以及“射、御、书、数等事,皆艺也,为卑为贱,为下为后”[53]。王阳明声称,“作圣之功”就在于“复心体之本然”,而与知识、技能不相关:“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54]他区分了良知与知识,认为“专去知识上求圣人”,则是“不知作圣之本”,“知识愈广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在“儒者之学,经纬天地”的儒学真精神的指导下,黄宗羲不但重视安身立命的圣人之道,也开始重视有助于民生日用的如律算、水利一类的“佐王之学”,反映了历史转型期的新风气。
四、“学之盛衰,关乎师友”——黄宗羲的正学术以挽世态人心的理想
正如上文所言,黄宗羲将恢复书院讲学治世精神,以救科举末流之弊,真正兴起人才,并将这些作为重建学统的努力之一。黄宗羲看到,欲兴起人才,关键在于“设学校之意”的重建。他认为,师友讲学,相互提契启悟,从而传承学脉,弘扬气节,振兴学术,挽救世态人心,乃至匡扶社稷政道与人伦。黄宗羲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反映在他早年参与结社、后来的抗清的活动中,也明显地反映在他晚年的讲学活动与著述中。
黄宗羲早年热衷于参与结社活动,他不仅是复社的骨干,而且还参加了杭州的读书社、南京的国门广业社、宁波的文昌社,与许元溥等人组织抄书社。此外,他还与余姚的昌古社、杭州的登楼社、石门的澄社的成员们有联系。他还对各社如鉴湖社、应社、小筑社、汐社等的不同情况有所描述。黄宗羲认为,崇祯间吴中创立的复社“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55],“其间楷模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56]。赞扬复社议论时政,“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政治得失。他认为“清议者,天下之坊也”[57],从而极力称赞主持清议的东林党人的气节:“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理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58]结社对黄宗羲气节观的形成,对他著《明夷待访录》与《留书》而批评时政,有很深的影响。他以明遗民自居,终身不仕清廷,可谓“大节无亏”[59]。
在清朝统治稳定后,黄宗羲专门从事讲学著书,以此传蕺山学说之余绪,主张“通今致用”,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虽说他早就从学于刘宗周,但真正理解刘宗周学说是在十几年之后:“公自谓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碍窒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60]康熙六年(1667),他在郡城绍兴与友人姜希辙、张奠夫等重开证人书院讲席,恢复由其师刘宗周创办而中断二十余年的“证人书院”。还选编了刘宗周的著作,从《刘子全书》的《学言》中辑录出《子刘子学言》,把他作为其师学说的精华所在。为补师说未备,撰写了《孟子师说》。为尊师说,在《明儒学案》前,收录了刘宗周《皇明道统录》中对部分重要明儒的评论;最后又专为其师撰写《蕺山学案》。
黄宗羲从乡邦学术文化发展关系天下兴衰,看到了学校在传承学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他赞扬“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说姚江人才之盛,是“吾姚江学校之功”,“三百年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搘定”。[61]他说“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62],并以王阳明、徐渭、杨珂的独立创作为例来说明。他表彰王阳明、刘蕺山对整个明代学术的贡献,说“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63]。就词曲而言,以为“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64]。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在鄞县举办“甬上证人书院”;此后,他长期在语溪、海昌、会稽等地转辗讲学,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在介绍黄宗羲的讲学盛况时说:“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在讲学过程中提出很多学术创新的思想,如主张“治学必以六经为根柢”,“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提倡学术争鸣等等。
黄宗羲认为,欲把握“学脉”之流衍,兴复经世之实学,必借助于新型师友之传承。他说:“学之盛衰,关乎师友。”[65]师友之所以共传“学脉”,就是因为不附会源流,不倚门傍户。说明这种师友关系,已非同于“释氏之五宗”为争偏正而聚讼不已的混乱与滑转,“儒者之学,不同于释氏之五宗,必要贯串至青原、南岳。夫子既焉不学,濂溪无待而兴,象山不闻所受,然其间程、朱之至何、王、金、许,数百年之后,犹用高、曾之规矩,非如释氏之附会源流而已”[66]。是有自得之实地承传,并不是要“附会源流”,在编撰《明儒学案》时,“此编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从禅宗的演变史来看,慧能去世后,先分为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两系。后南岳又衍为沩仰、临济两宗,而青原则歧为曹洞、云门与法眼三宗。此“释氏之五宗”至明清之际,沩仰、云门与法眼三宗基本上已销声匿迹,唯曹洞、临济两宗尚存。但这两宗为争论优劣而聚讼不已,并各自从师承传授关系上去找权威性的根据。黄宗羲主张对于“两家之是非,不必为之辨”,因为他们只争门户而无创见:“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者也;今之学佛者,倚傍门户者也。自立门户者,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门户者也,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凉。”[67]黄宗羲曾指出:“陆王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朱子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之入门,各有先后,此其所以异耳。”从“学脉”流变角度看,陆王与朱子“固未尝分”:“非尊德性则不成问学,非道问学则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复性言学,陆子戒学者束书不观,周、程以后,两者固未尝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时教法稍有偏重,无关学脉也。”[68]不应从教法的偏重来分朱陆门户,而要多关注学脉传承。
黄宗羲通过弘扬师道,传续学脉,重建“设学校之意”。他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认为,学校要“养士”,“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学校应如东林书院与复社,提高士权,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议政,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君权与士权、朝廷与民间、政统与学统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获致政治统治的良性运转。
五、“各持一说,以争鸣天下”──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
黄宗羲正学术以挽救世态人心的努力,还集中表现于他对学术民主的建设上。在黄宗羲,“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轻易唯诺以随人”[69],认为治经为学,亦应“各求其是”,不人云亦云,反对“守一先生之言”。黄宗羲指出:“夫穷经者,穷其理也。世人之穷经,守一先生之言,未尝会通之以理,则所穷者,一先生之言耳。”[70]他主张“以理会通”诸经,不株守一家一人的定论,有着鲜明的学术平等思想。他大力表彰了有着创新精神的王阳明,多次阐发王阳明“学贵得于心”的思想,力倡“各求其是”,他不同意时论“因阳明于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谓其糟粕《六经》”[71],认为这是冤枉了王阳明。
黄宗羲痛斥那些屈从“时风众势”的“黄茅白苇”之学,反对学无自得,倚门傍户,人云亦云,批判“时艺”、“时文”等“场屋之风气”之弊,更批判“选家之风气”,因为“自是以后,时文充塞宇宙,经史之学,折而尽入于俗学矣”[72]。“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73],不必拘于“家数”,主张“各持一说,以争鸣天下”[74]。
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为《宋元学案》发凡起例并撰写重要学案,可以说对宋明学术流变了如指掌。他尤其对“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75]的不正常的学术现象,进行了哲学批评。当时学者关注“时艺”、“时文”,株守朱子学说,谨小慎微,不敢越理学矩矱半步,宁肯守人“成说”,“泥而不通”,不肯“会通以理”。薛瑄、吴康斋与胡居仁,是明初公认的大儒,但他们恪守程朱理学,在学术上毫无创见。如薛瑄就明言:“自考亭以还,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对于吴康斋而言,黄宗羲说“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76],到陈献章才出现了新的学术气息,他敢于独立思考:“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77]虽然陈献章有吴康斋门人,但却强调自得,为吴门“别派”。
学界生机黯然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朝廷对“一先生之言”的推重,“使天下一尊于朱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78]以程朱注疏为科举制度下取士的最高也几乎是唯一的标准。这样,社会上、学界内“一定之说”充斥,扼杀了学术应有的生机,社会上甚至出现了明儒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所言的的奇怪现象:“自有宋儒传注,遂执一定之说,学者始泥而不通,不能引伸触类,夫不能引伸触类,亦何取于读经哉?”(卷一)何良俊还说这还导致当时的俗儒“宁得罪于孔孟,毋得罪于宋儒”(卷二)。明代四川学人杨慎也指斥当时令人“惑”的畸形学术发展:“今之学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79]可见当时的情景确实令人忧心忡忡。黄宗羲主张“学问与事功并重”,认为“道本大公”,通达“道”之进路并非只有宋学一途,更非朱子学一门可当圣人心性之学。
黄宗羲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他在书院讲学中,提倡学术争鸣,比起“守一先生之言”的章句之学,更能体现他的学术平等与自由争论的思想。“黄宗羲学术民主思想的内容之一,就是强调自得精神,主张创新,反对附从他人。”[80]康熙十五(1676)年至十九(1680)年,黄宗羲应知县许酉山之邀,讲学海宁,倡扬新的学风,鼓励“辩难”,“每拈《四书》或《五经》作讲义,令司讲宣读,读毕,辩难蜂起,大抵场屋之论,与世抹杀”,摒斥俗儒腐儒的“场屋之论”与狭隘习气。他要学生学习经世致用之学,还写了《留别海昌同学序》,抨击“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脱离社会的学风。他还叮嘱学生:“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81]认为学问追求“用得着”,反对“附会一先生之言”的“场屋之论”,学不适用,空依“成说”,妄自代圣人立言,所学不过是“糊心之具”。
这是他批判整合理学与心学,特别是总结阳明心学,接续其高扬主体意识与学术个性,提倡贵在自得的学术精神,所结出的硕果。王阳明曾主张“反之于心”,以求“良知”之“是”:“先儒之学,得有浅深,则其为言,亦不能无同异。学者惟当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所同,亦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是而已。”[82]他所强调的正是“自得”,“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圣人之道”[83]。他指出,“先儒之学”亦是参差不齐,因“得有浅深”而“言”也会有差别,不应该简单地表示赞同,或故意挑剔反对,应该以自己的“心”(良知)去审定。王阳明认为“良知是自家的准则”,以此标准去作判断,来求之于“心”(良知)的“自得”。王氏主张讲学当实有其用:“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84]
黄宗羲赞成求“道”为“学”时,要真切体道,“当身理会”。他多次赞扬“相反之论”、“异同之论”,反对“以水济水”毫无创见的雷同重复,他说:“古之善学者,其得力多在异同之论,以水济水,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耳。”[85]尤其不喜欢那种为科举准备的“守一先生之言”的“讲章”:“余生平颇喜读书,一见讲章,便尔头痛。”[86]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为真,凡倚门旁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轻生之业。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者也。”在东林书院讲席方盛时,北直隶河间人耿橘修复虞山书院,当时有一位叫左宗郢的御史前来讲学,说了一段“当时皆以为名言”的话:“从来为学,无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学问只在人自肯寻求,求来求去,必有入处,须是自求得的,方谓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87]黄宗羲的“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为真”,与左宗郢的话最为相似。说明独辟蹊径地自求学问,上接心学对个体性的高扬,已经成为时人所认同的方式,这也被黄宗羲所大力提倡。
由上述可知,为了应对空疏学风与明清鼎革的双重影响,世态人心的沉溺与学术对政治的疏离,黄宗羲力主重建学统,读书以求达世用,而非仅“讲以口耳”,以取科举功名。一世“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小儒”们只有奴婢心态,而无应对现实急难的良策。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条“有亡国有亡天下”之分:“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一家一姓败亡,是其小者;文化沦没,才是尤其堪忧的。黄宗羲正学术、挽人心,当亦有这种意识在其间。故尔,他在“天崩地解”之际,表彰有“佐王之才”的“豪杰”之士。
黄宗羲不仅从制度设计上“条具为治大法”,而且从更深的层面提出学统重建的观念,弘扬学术真精神,激发士人学术承担意识,提倡豪杰经世的理想人格。梁启超在论述黄宗羲等晚明遗老的学术活动时,说他们是“以学术为政治”的。如果再从学统重建的视角重新审视黄宗羲的著述,我们将会有一些新的推测:不仅《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及碑、版、传、状类著述,包涵着黄宗羲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社会批判,而且即使是黄宗羲纯学术史著述如《明儒学案》,也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在内。[88]简单说来,“学案体”著述的哲学特质之一,就是对各家宗旨钩玄提要,使学脉流衍秩然排列,将明代儒者的传道谱系予以疏释,供后之学者择取诸儒的“得力处”。不无可能的是,黄宗羲希望后学能从“学案体”著述中获取经世致用的资源,由一代学术之史探察一代兴衰治乱之故,由学术传承寻绎时代担当的识见与努力的方向。对于这一问题意识的详细开掘,须尚俟他论。
[①]柳亚子:《关于读经问题及其他》,《学习与生活》第4卷第5期,1943年5月。
[②]熊十力:《读经示要》,重庆南方印书馆1945年,第209页。
[③]钱穆:《学统与治统——政学私言五》,《东方杂志》第41卷5号,1945年8月。
[④]贺麟:《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⑤]张东荪:《中国的道统——儒家思想》,《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⑥]牟宗三:《略论道统、学统、政统》,《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⑦]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267页。
[⑧]参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201页。
[⑨]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7-178页。
[⑩]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⑪]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⑫]陆九渊:《与唐司法》,《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96页。
[⑬]《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第411页。
[⑭]黄宗羲:《清溪钱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51页。以下所引《黄宗羲全集》,均为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不再详示。
[⑮]黄宗羲:《余姚县重修儒学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34页。
[⑰]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33页。
[⑱]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⑲]黄宗羲:《姜定庵先生小传》,《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623-624页。
[21]黄宗羲:《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88页。
[24]黄宗羲:《进士心友张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00页。
[25]黄宗羲:《南雷诗历•脚气诗》,《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338页。
[26]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0页。
[2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10页。
[28]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页。
[29]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页。
[30]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36页。
[31]黄宗羲:《振寰张府君墓志铬》,《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39页。
[32]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645-646页。
[33]《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34]王阳明:《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0-231页。
[35]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一,《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1页。
[36]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一,《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
[37]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一,《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38]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改本(四稿)》,《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375页。
[39]《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
[46]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49]《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93。
[50]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51]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52]《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93。
[53]《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93。
[54]《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55]黄宗羲:《刘瑞当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335页。
[56]黄宗羲:《刘瑞当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335-336页。
[59]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下册,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84页。
[61]黄宗羲:《余姚县重修儒学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33页。
[63]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21页。
[64]黄宗羲:《胡子藏院本序》,《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61页。
[65]黄宗羲:《陈夔献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54页。
[66]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5页。
[67]黄宗羲:《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85页。
[68]黄宗羲:《复秦灯岩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10页。
[69]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五册,第279页。
[72]黄宗羲:《冯留仙先生诗经时艺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2-43页。
[73]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204页。
[74]黄宗羲:《吕胜千诗集题辞》,《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08页。
[75]黄宗羲:《孟子师说·题辞》,《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48页。
[78]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年。
[79]杨慎:《先郑后郑》,《升庵全集》卷七十一。
[80]朱义禄:《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81]黄宗羲:《陈叔大四书述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4页。
[82]王阳明:《书石川卷》,《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
[83]王阳明:《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84]《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85]黄宗羲:《答忍庵宗兄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26页。
[86]黄宗羲:《陈叔大四书述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4页。
[88]笔者前此对黄宗羲“学案体”著述作过初步的研究,如(1)黄敦兵、雷海燕:《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兰州学刊》2007年第2期,第31-33页、第104页;(2)黄敦兵:《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意义──以<王畿学案>为中心》,见吴光主编:《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19-231页。但都没有从学术与政治相互关联的角度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