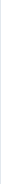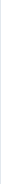编者按:当代绍兴乡贤陈桥驿先生是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前不久,陈教授就越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接受了我中心的访问,现刊发部分,以飨读者
专家名片:陈桥驿,浙江绍兴人,1923年出生,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在历史地理学、郦学、历史地图学、地方志和地名学研究、城市研究、古都研究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卓著,著有《淮河流域》《祖国的河流》《水经注研究》1-4集、《郦道元评传》《水经注校释》《郦学札记》《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吴越文化论丛》等学术专著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地理学报》《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各类论文400多篇。曾赴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多所大学访问讲学。国际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咨询委员,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荣誉委员。

越文化研究分广义越文化研究和狭义越文化研究
越文化研究是地质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要从地理概念来理解这个问题,陈教授认为首先要明白越文化研究分狭义的研究和广义研究。在这两者中,基础是狭义的研究。广义研究是狭义研究的拓宽和发展,所以我们要研究越文化,必须要先打好狭义研究的基础,越文化的狭义研究的基础就牵涉到越族。
我们要做早期狭义越文化研究,研究越族的早期发展史。吴越争霸是下一个环节,越王被俘,失败回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逐渐国富兵强,公元前473年,灭吴。句践北上争霸。公元前468年,越迁都琅琊,后又回到越地,直到秦统一六国。秦一统后,秦始皇说:“东南有天子气”,意为东南越地要造反。于是借祭大禹为名,强迫越族移民到钱塘江以北、安徽以南一带。还有一些人逃到中国西南一带,所以今天西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地名发音跟绍兴一样。比如含“吴”、“句”、“朱”、“余”等地名。这些都在《越绝书》中有记载。秦一统后,还有一部分人,既没有服从强迫移民,也没有逃到其他地方,他们自己就逃到山上,称“山越”。浙江有好多这样的“山越”,一直等到三国以后才陆续下山来。这就是狭义上的越文化,他跟越族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越的很多风俗习惯都保留下来了,不仅是绍兴一带,整个浙江以及江苏南部都是越的后代,越的分子。对于这些地区的相关研究都属于广义的越文化研究范畴,范围是很广的。我们现在越文化发展出现了狭义越文化和广义越文化之间连接关系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比较起来,现在国内主要是狭义的研究做得比较多,广义上的研究还不够,因为广义研究是以狭义为基础的。
越文化研究的历史
关于越文化研究的历史,陈教授指出,我国史籍最早记录越人活动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1世纪末):“于越来宾”。 这一条可以视作信史,其时距良渚文化的下限不过一千年。
按照先秦人物的年代排列,管仲是最早提及这个地区的人:“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管子·水地》第三九)。几句话,把当时越地的自然环境和越人的低劣素质和盘托出。我们宛如看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一幅图画:在一片潮汐出没、沮洳泥泞的沼泽地上,一批断发文身、又脏又赢的蛮子,在那里挣扎生活。
以后是墨翟,他在世稍晚于越王句践,所以听到一些句践练兵的残暴传说:“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知其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能胜数也”(《墨子·兼爱下》)。越人好勇,这是普遍流行于“中国”的南蛮故事,类似的记载不少。
越国是在战国七雄之前最早称雄的国家。它囊括了从今山东东翼直到今钱塘江以南越故地的大片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必然都有较大发展,可惜我们很难从文献资料中检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先秦的“中国”文献中,只记及它的武功,如《墨子·非攻下》:“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对于于越来说,这些先秦“中国”文献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由远离越地的汉人按当时流行的传说写成的文字,对于越史特别是越文化,后世的研究者不免有一种 望和鸟瞰的感觉。因为从这些文献中,人们看到的于越,还仅仅是一个并不清晰的轮廓。所幸于越自己还留下了一宗重要的文化遗产,即越地越人的文献《越绝书》。此外还有少量在东汉之初身居越地的学者们的著作,成为后人研究越文化的重要源泉,比如王充的《论衡》,尽管它并非专叙越地越事,而且今本也有较多缺佚,但由于王充是一位博学多才、见识超群的学者,所以《论衡》中记及的越地越事,实在不同凡响,王充也不愧是一位科学地研究越文化的前驱。
近代对越文化的研究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见识宽广,根底扎实,治学勤奋的史学家,他们既深入钻研古代有关越人的大量文献,又细致地鉴别分析这些文献,先后提出了不少前无古人的科学创见。如顾颉刚、罗香林、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诸氏,都发表过不同于前人见解的论文。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越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获得了大量的成果,其标志:第一是研究者的队伍空前扩大,若干高等院校也加入了这种研究的行列,并且还建立了几处越文化研究所,有稳定的研究人员;第二是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为了交流和讨论这些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曾经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第三是相关学科的进入,在研究队伍中,除了以往的历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民族学者和部分考古学者以外,地质学、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者等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而原来的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必须依靠先进的旁支学科的研究成果,过去从文献里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往往可以迎刃而解。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越文化研究者对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的实勘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值得学术界特别是越文化研究者重视的。
应该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来研究越文化
陈教授指出越文化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能光靠历史学、考古学。而是包括地质学,地史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另外地名学也很重要,比如说“余”(yu)字,余姚、余暨(萧山古称),它们都靠海的,“余”在这里是“盐”的意思。从舟山群岛起一直到萧山,“一”、“二”、“三”这些数字的发音跟日本越族发音也有共同之处。
另外人类学也很重要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人文人类学。现在主要是体质人类学研究,如果要更全面研究,那么也需要人文人类学。可见多学科合作是很重要的。这样越文化研究发展才有前途,现在越文化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我们应该加强跟国外的沟通。外国学者对越文化也有进行深入研究,日本研究很精、很细,美国侧重宏观理论,大框架研究。他们研究越文化的资料是很丰富的,比国内还要丰富,比如关于湘湖的资料就比国内全。关于绍兴的地方的研究,有些资料也是国内没有的,比如James.H.cole 出了一本《Shaohsing: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比如《Xiang Lake: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很多国内学者研究湘湖就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陈先生认为越文化研究还要加强国际交流,从1983年起,陈教授先后受聘担任日本关西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等学校的客座教授,并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讲学,开过《中国历史地理》《水经注研究》等课。
最后,陈教授指出,在越文化研究中,我们首先要端正学风,防止学术腐败和政治腐败。越文化研究的主要误区是研究者读书少,知识面不广。对一些资料不亲自查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我们既要发扬乾嘉学风,又要提高外语水平,只有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我们的越文化研究才更有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