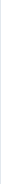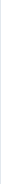研究越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根据历史发展的轨迹,需要从三个阶段来分别来阐述,即秦汉之前、秦汉之际和秦汉之后。秦汉之前应是越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在独立的生存空间中自主地滋生和发展着;秦汉之际是通过争霸的兴衰和进退,直至秦灭六国、试图强制性统一文化到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越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秦汉之后是在大的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在融合主流文化和地域特色的过程中,展示、丰富着越文化的特有个性。
中华文化来源是多元的。从地域上看,有陕甘地区的商周文化,有川渝的巴蜀文化,有江浙的吴越文化,后来又有齐鲁文化、楚文化等等。但是,后世所谓中原文化,实际上就是商周文化,逐渐成了主体。①
在大中华这个历史研究单位中,还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个性”鲜明的地方社会,从而形成许多地区文化单元,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等。除了中华文化这个共同的“母亲”之外,这些大大小小的区域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母子”文化关系,而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它们通常是分别形成的,而不是垂直衍生的。中华文化是一个由多民族、多区域文化百川归海汇聚而成的一体多元的大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成长的摇篮,黄河流域的周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吴越文化曾经极大地推进了炎黄文化的发展。李阳春认为,建立在粟麦农业基础上的中原周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标榜。儒学志在钟鼎,追求经世致用,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由此滋生了伦理规范和内省模式。建立在水稻农业基础上的南方楚文化,因道家文化而著称。道学留连山林,向往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而耽于幻想。人们概括其特征是:“北方重辨证,南方重遐想”;“中原重礼信,荆楚重情感”。②事实上,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水稻农业的发源地是属于越文化的核心地区余姚河姆渡遗址,楚、越文化也不存在一种相互从属的关系。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黄河上中游文化区系及与之相对应的炎黄部落集团东进,黄河下游、古河济之间文化区系及与之相对应的太白皋、少白皋部落集团西进。两者相汇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撞击和交融,于是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并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三族至西周已基本融成一体,产生了认同的族称夏,而西周分封的诸侯众多,同属诸夏;有了认同的祖先黄帝(炎帝是黄帝的兄弟);也有了认同的区域区夏(即夏区);认同的语言雅(夏)言,还形成了以象形为基础,“造字六法”已具雏形的文字,即保存在甲骨和钟鼎等遗存上的文字。至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开始代替铜器,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早在商周之际在河陇地区及北部草原边缘已出现的号为戎狄的游牧人,此时征服了草原,而且和草原及原始森林边缘固有的狩猎人[1]群相融合,形成了中国游牧区的诸部。中国南部则是从事水田农耕的诸部。
夏、商、西周三代及春秋战国,即通常所说的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元典时代。期间大约超出了2000年,与起源时代数以百万纪年相比,显得非常短促,然而,在有文字以来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中,仍是一个漫长而古远的历程。
当时天下纷争,华夷交侵,诸说并起,而夏商周,其中尤其是西周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被奉为元典。以三代礼乐为主导,同时也吸收涵化了四夷文化,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竞长,文化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一些原来被诸夏视为戎狄或蛮越的诸侯,如吴、越、秦、楚一跃而与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同列。
在文化人类学上,“区域”这个概念与“地区”是不同的,地区是一个伸缩性强、方便使用的模糊概念;而区域则是根据一定标准,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的地区,因此,它必须能以同样的标准与相邻或不相邻的地区区别开来。①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区域的文化大致是以独自的轨迹在发展着,以越国中心区域为核心的越文化也是如此。“当是时(秦统一时)还存在着三个文化圈,或称体系。这就是齐鲁三晋的中原文化,秦的西部文化和南方的楚越文化”。②
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楚、越同属于蛮夷。黄河流域诸国不许楚国问鼎中原,明白地把楚国排斥于黄河流域的舞台之外。而楚庄王问鼎受阻,犹自以为“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遂掉头东进,实即自视楚与中原为两个历史文化系统。“楚文化北向受阻,中原诸夏对楚的排斥,这种南北对峙正是江河两大流域的文化差异的集中表现。即使到战国,虽然两大流域的民族接触与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但楚犹未脱蛮夷之俗,原来的民族的与文化的差异仍然存在,仍然明显”。③“楚曰:‘我蛮夷也’”、“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史记·项羽本记》)等言论,就是这种差异及对抗情绪的反映。再进一步而言,楚、越文化虽同被中原文化视为“蛮夷”,但又是缺少相互依存性的文化个体,是在不同的源头上依照独特的发展轨迹运行。
一种文化的独特性,源于生存方式的独特性,我们认为越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立发展起来的源头之一,是因为越地先民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方式。首先表现为独特的生产方式,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早在7000多年前,已经开始了稻作栽培,在1973年和1977年的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萧山跨湖桥遗址中有发现少量稻谷,而时间上有明显早于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500-8000年。江南稻作农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外辐射传播,严永明先生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和众多的阐述。
从生活方式来看,地处江南的越人与黄河流域的原始居民有着极大的差别,以居住而言,北方的居民是依山穴居,而越人的生活环境是临水为家,缺少穴居的基本条件,但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在实践中创造了全新的居住建筑样式即“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这种建筑的遗址:“这次出土的木构件总数在千件以上。主体构件是十三排桩木。这里至少有三栋以上建筑。这座建筑的原状可能是带前廊的长屋。根据以下几点判断,建筑应是干栏式:(1)建筑所在地段为沼泽区,地势低洼潮湿,需要把居住面抬高。(2)建筑遗址内没有发现经过加工的坚硬的居住面。(3)推测为建筑的室内部分,发现有大量的有机物堆积如橡子壳、菱壳、兽骨、鱼甲、鳖壳以及残破的陶器,等等。这些应是当时人们食用之后丢弃的。如果不是把居住面抬高的干栏式[2]建筑,室内这层堆积物的形成是无法解释的。(4)所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是排列成行,达入生土的桩木,此外为失散的梁、柱长木以及长度均为80——100厘米的厚板,绝无高亢地区建筑遗址所常见的草筋或红烧土之类,说明此处建筑全系木构。”④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建筑方式也非楚地所具有的。
再从风俗语言等方面看,与华夏文明相比,越文化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先秦典籍中屡屡提及越地民俗特点如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萁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信仰等,成为区别于中原礼乐文明的显著特征。“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①原始习俗折射出他们生存的艰险。图腾崇拜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理解,也反映出一个区域的文化认同。越先民从早期发自内心的对鸟的仰慕,到由于对江海怒涛的恐惧而产生的对龙的崇拜。江南沼泽地是鸟类栖息和繁殖的理想场所,鸟类也是当时与先民共处于这片土地上的最大众的生灵,鸟类有当时先民所难以企及的自由和悠闲,以及某种神灵的“启迪”,河姆渡遗址“双鸟朝阳”的精美图案;良渚遗址玉琮、玉璧上的鸟图象,绍兴的越族铜鸠杖都留下了鸟崇拜的记号,把人的“长颈鸟喙、鹰视狼步”看成是帝王之相,甚至将越人的语言也称之为“鸟语”。断发纹身的习俗是为了避免蛟龙之害而发明的自我保护方法。
此外,在文化技艺等方面,有以精妙绝伦的越王剑为标志的精良的青铜铸造技术,发达的造船业,奇特的文字——鸟虫书,以及丰富多彩的陶瓷手工艺。
从有考古依据的8000多年前到有文字记载的于越先人开始加强与中原的联系,其中的几千年时间里,越文化可以说是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着,其发展的成就也就必然成为融入中原文化中的重要因子。
中国的大统一,以诸夏统一为汉族作主干,又在各民族形成地区性统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经历了南北农牧各族由多元向一体聚合的过程;大一统分裂了,重新在地区性统一的基础上形成更高度的统一,直到完全确立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从孔子述《春秋》开始,继之以孟子及法家诸先辈不断阐明,大一统成为“《春秋》之要义,大地之常经”。不断发展巩固中国的统一,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追求目标,是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民族大义。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汉族在两汉已形成统一,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凝聚结合的核心。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体和主导,同时中国各民族都保持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与汉文化共同构建了多彩多姿、多元[3]兼容和相互涵化的中华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及后来的秦末战争为南北文化的交往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契机。根据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民族及文化在迁徙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往往产生出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结果。战争是集团性的民众的武装迁徙与流动,几个存在文化差异的集团之间的战争,必然会引起文化的交互渗透。南北诸文化圈经过战争的洗礼,得到更加全面的接触交往。大一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待其他区域文化的观念也在文化的交往中逐渐改变,不再狭隘地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仇视及文化拒斥观,而开始能以全新的视角,从国家政治统一稳定的需求来审视原本以为“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庄子·天下》)的文化体系。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由于秦始皇雷厉风行的变革,“民族要素的几个方面,即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到秦统一时大体都具备了”。②首先,秦代通过修长城、凿灵渠、建驰道和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华夏族共同的生活地域;其次,度同制,车同轨,使得华夏民族共同的经济基础得以建立;再次,秦规定“书同文”,先是以小篆为标准文字,后以隶书作为日用文字,从而结束了战国“文字异形”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各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央政权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最后,“行同伦”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统一。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秦始皇凭借强将劲弩利剑推进了文字、货币、道路等器物制度层面的统一,“速成”了统一中华的“硬件”。秦朝统治者还试图统一天下的思想,以秦文化化天下。秦朝统治者用同一化的政策来化解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矛盾,的确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变迁,但从文化变迁的层面来看,它主要属于物质层面的变迁,即文化人类学所谓的直线式变迁或外部式变迁。这种变迁主要是由外部条件直接引起的,在变迁历程上大都呈现直线型的特点,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与其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要素比如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等的变化。文化变迁更关键的在于促成非物质层面的变迁。非物质层面包括观念层面、行为层面、心理层面等广阔领域,相应就形成了与文化观念、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等相关联的文化变迁问题。非物质层面的文化的变迁依靠强制性是不能完成的。秦末战争中,楚人破釜沉舟的反抗和楚文化的强烈反弹和复兴是其中一例,越人“锐兵任死”的长期反抗,也导致了对越人几次强制性的北迁。
据有关专家考证,汉族形成于两汉时期,在两汉以前,汉族还未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之前,中华文化是经过各民族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以及分流之后,逐渐形成的。在中华大地上文化的起源是多区域、多元化的,同时,这些不同的区域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存在着交流和融合。在汉族形成之前,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原地区处于北方畜牧、旱作文化与南方农业、稻作文化的交汇点上,这种特殊的地区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得以中原华夏民族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即汉文化。
对于越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在秦汉之前是多渠道、多途径的。首先人才的流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越王句践的左膀右臂都不是土著的越国人,而是来自与楚国,文种本是楚国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缘于吴越战争,而当时楚王又不满吴王,有心助越抗吴,就派遣他作为使者到越国担任谋士。范蠡出身农家,生活贫困,是楚国的才子之一,其时随文种一起来到越国,句践对他们的到来非常重视,并不囿于成见,很愉快地接纳了他们,而且视他们为座上宾,委以重任。文种的“伐吴九术”(《史记》称“七术”)对雪耻报仇起了巨大作用,也成为越文化几千年来形成重智谋特征的肇始者;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为上将军。①此外,大夫计然,“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集解》)据记载,计然为越国复兴制定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把“农末俱利”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视为治国之道,“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山之上,乃用范蠡、计然,……报强吴,观兵中国,号称五霸。”他与范蠡一起成为中国重商、经商的祖师爷。
连年的征战,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交流[4]的作用,吴越争霸及进而争霸中原,使得原来僻处东南,远离中原,本来处于相对孤独的越人,自然而然地经受了而中原文化的交流,《越绝书》(卷八)的一段记载,说句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晋见,为述五帝三王之道,句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不论此论可信以否,面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是不争的事实。在相互交往中实现文化的融合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无论是越国与吴的交恶,还是与鲁、楚交好,都较为普遍在存在着人员的往来和财物的馈赠。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把越文化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如造船、琢玉、青铜铸造等技术的广为流传,许多诸侯国把越国青铜剑视为罕世珍宝《庄子刻剑》载:“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另一方面,越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也广泛地吸取了中原和周边国家的文化成就,从而使越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的建设上,不少是沿用了商周的旧制;在诸如尊、鼎、爵等青铜礼器上,大多含有华夏文化的色彩;在建筑墓葬上,受到楚人的影响较大,如公元前490年越国都城的设计源于楚廷,其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又与中原许多古城的构建相类似。
真正实现文化的融合是在强制性和自发性的大迁徙中加快完成的。秦汉时期有三次对于越族的大规模强制性北迁。第一次发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游会稽,迁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故鄣。又迁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此次迁徙广而分散,目的是为了防备于越“锐兵任死”的反抗,以弭息动乱。①第二次北迁是在汉代初年,由于越民比较集中[5]的浙南、福建、两广等地,东瓯、闽越和南越又屡起事端,故汉武帝在用武力镇压其暴乱后,沿用秦始皇分而治之的方法,强迫越人北迁。第三次,也是汉武帝时期,对东瓯、闽越的北迁,公元前138年东瓯遭受闽越攻击,向汉求援,武帝遣军救之。东瓯为免受再次攻击,“请举国徙中国”,于是,汉命东瓯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至公元前110年,闽越内讧,武帝又乘机下令:“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②
与强制性迁徙不同的是自发性的南迁。因为是自发性的,所以,迁移的时间很难有准确的划定,但大致的迁徙路线有两条,一是“走南山”,从公元前333年无彊伐楚失败后开始,不少越民为避祸移居浙、苏、皖、赣、闽、鄂、湘等地的山区;二是漂洋过海,到达台湾、东亚和南亚各地。
说是大规模的迁移完成了文化的融合,一是因为越地的原住民已经离开了原来赖以生存的环境,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只能融合进当地的文化,才能立足,所保存的只是原有文化的某些基因,如某些习俗、语言等,并会对当地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二是越地空虚后填补进来的基本是中原的居民,他们成为越地的主流居民后,带来的中原文化也就必然成为越地的主流文化,但是越地原有的文化因子及越地的生活环境,不能不在这种主流文化的流传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表现出某种独特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吸取亡秦教训,遵循“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为实现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西汉的开国元勋及思想家们认识到,诸文化体系虽然有所偏颇,但都有不可弃之理: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序君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皆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百家都有其特定的发祥地与影响域,比如道家之于楚,儒家之于齐鲁,法家之于三晋,往往成为区域文化的象征,成为区域文化的代名词。对待百家的态度其实也体现着对于区域文化的态度。通过文化整合来促使文化的统一,即使异质文化在经过文化接触后产生一种同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代表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体系,初步完成了民族文化的整合,越文化也就融入了主流文化。
在接受中华文明洗礼后的一千多年中,越文化保持着明显的差异性,但就性质而言仅属于同质文化的区域性差异。这是我们探讨文化大一统后的越文化特征的基本前提。
以吴越两地而言,虽然大而言之可统称为吴越文化,但在发展还是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虽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承认差异的存在。如有的认为吴文化在成熟后更多地趋于典雅、精巧、藻丽和柔弱,而越文化却经常地保持着一分通俗、朴野、素淡乃至刚猛气息。但是董楚平先生认为:柔、细、雅,似乎可以称得上七千年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换了人间”,换了时间,换不了这些地域特征。并以七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一个地方的艺术品,能像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那么精致、柔雅,富于想象力?及良渚文化玉雕的精致高雅、吴越争霸时的精致兵器,当时最美的文字鸟虫书等为证,进而指出秦汉以后的柔、细、雅的气质显得更为突出。
笔者认为,分析同质文化的区域性差异,需要考虑众多的因素。首要的因子是生存环境的特点,只要生存环境的继续保持,原有文化必定会得到较为完整的保持。作为越文化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江南水乡的大环境是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稻作栽培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也是基本得到了保持,这使得原有文化的长期保持有了基本的条件。
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越文化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随着原住民的大量外迁移,各地居民的逐渐填充,使得文化承传的主体有了很大的不同,二是生产生活环境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如绍兴地区鉴湖的修筑,极大地改变原来穷乡恶水的面貌,真正成为鱼米之乡;三是文化的政治环境也有了根本的区别,越文化是在诸侯争霸的背景下成型的,争霸复仇的因素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两汉三国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越地处于远离政治中心,远离逐鹿中原的战场,并成为中原居民躲避战乱的理想避难地,并且大量的豪族仕绅、文人墨客的涌入,进一步丰富着越文化的内涵。
因此,认为越文化经常地保持着一分通俗、朴野、素淡乃至刚猛的气息,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越文化的底韵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气息;同样认为越文化存在着柔、细、雅的特征,也是有着强烈的说服力,可以有许多佐证。如此的矛盾性就是越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长期的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和日益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在越文化的中心区域的人们特别是文人的身上表现出雅的特征,文风日盛而被称之为“江南人文薮”,重知识的探求、艺术的熏陶,尊教重艺成为经久不衰的民风,使之成为名士荟萃、人才辈出之地。魏晋南北朝以来,涌现出了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但是有一点与其他地域是明显地不同,即在重智慧、重艺术的同时,更加重智谋。越地居民大换班后,重智谋的特性并没有随之消失。在南宋的多难之秋,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抗金复国要“以越事为法”,其中就有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王十朋作《会稽风俗赋》,将越事概括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隐忍成事成为越人报仇雪耻、发愤图强的主要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所谓隐忍成事,强调的是深沉、内敛、务实,追求在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动之中获得成功,力求避免正面冲突,通过委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行为范式。正因为重智谋,所以越地的文人较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更看重的是经世致用。
同时,原型文化中的那种卧薪尝胆、“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性格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在历代的越人中,特别是“有骨气的文人”中,每当面临大义抉择时,都会从骨子里迸发出一种尚武的豪气和强烈的复仇意识,表现出一种刚烈、豪气,面临大是大非和民族危亡关头所散发出来的骨气。但它表现出来的不是图一时之快的慷慨悲歌,快意恩仇,而一种“面壁十年图破壁”的深谋远虑,是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
秦汉以后的越文化就是一种刚和柔矛盾统一、文雅和质朴有机结合、重智慧更重智谋水乳交融的区域文化,并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①许嘉璐:《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史哲2004年第2期
②李阳春:《湘楚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内涵———兼论优秀民族精神的培养》求索,2004年第3期
①罗义俊:《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文化》,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②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页
③参见《文化学辞典》第50页“区域”条;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④《考古学报》1978年第一期发表的浙江省文管会、博物馆有关《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
①《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69页
②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3页。
①《越绝书》卷八、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