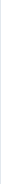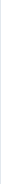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文物》1999年第11期发表《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其“结语”明确判定“印山大墓即为史书记载中的‘木客大冢’,大墓主人是越王允常。”[1]文中所说的“史书”主要指《越绝书》。
《简报》作出如此具体明确的结论,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而是仅仅凭借经早年彻底洗劫剩下的一鳞半爪的出土遗物的年代判断与对《越绝书》几句模糊的记载所进行的一种推论。但是,允常在位不过十数年[2],而判断出土物的年代范围不可能缩小到允常在位前后那几十年之内。《简报》对《越绝书》有关记载的理解,大有商榷余地,绍兴当地学者对印山是否《越绝书》中的“木客山”,至今尚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印山大墓的规模气势,与允常时期的越国国力相比过于悬殊,它只能是越灭吴后,国力鼎盛时期某位越王的墓葬,具体人物尚难明确判定。学术研究要实事求是,有几分材料讲几分话,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宜轻下过细的结论。
印山大墓早年经过彻底洗劫,筑墓时的遗留物仅剩50多件(组)玉器、石器、青铜器、漆木器和几件器形不明的残陶器等。其中,主要是玉器,有31件(组)。玉器是耐用品,使用年代跨度很长,吴越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玉器的器形、纹饰不可能有明显区别。最能判断年代的本是陶器,但印山出土的陶器都已十分残破,连器形都无法辨认,更无法从中判断年代,即使器形完整,能判明年代,也未必能在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印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铜器和漆木器的主要纹饰是卷云纹,卷云纹不但见于春秋晚期吴国墓葬与窖藏的出土物,也见于战国初期的绍兴306号墓出土的玉瑗、玉琥、龙形玉佩、圭形玉佩、蝉形玉佩、方形玉饰等众多器物[3]。综上所述,这些筑墓时的遗留物的年代,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
[2]允常卒于公元前497年,何年即位,史书缺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舆地志》说:“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周敬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19年至公元前476年,历44年。这期间,越国经历夫谭、允常、勾践祖孙三代。《史记·越王勾践世有》说:“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五年。允常即位时间当在阖闾元年至五年之间,距卒年分别为18年与14年。
[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应该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至于填土与封土中捡出的陶片与原始瓷片,《简报》认为“应是原取土地点就已包含的遗物”不是筑墓时的遗留物,年代应比筑墓时略早。如果这些陶片与原始瓷片的年代为春秋晚期,那么墓葬的年代就可能是战国初期。其实这些陶片的纹饰,主要见于战国时期。例如印山大墓最多见的方格纹,是战国时期浙江常见的印纹陶纹饰。
1998年5月13日,印山大墓的发掘单位在绍兴向社会公开发布消息,定印山大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至于墓主人只说“当为越国某位君王”。稍后,发掘单位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定位。[1]这是根据现有资料所能作出的结论,下这样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只隔一年时间,墓葬的年代范围就缩为“春秋末期”。在这一年里,印山大墓并没有出土新的遗物,年代的改判完全是跟着“允常”转。因为在这一年里,浙江一些学者论证印山大墓即为《越绝书》所说的“允常”“木客大冢”,墓主人确定后,墓葬的年代范围也就随之缩小。那么,把墓主人定为“允常”,是否正确呢?下面让我们重点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简报》论定印山大墓为允常之墓的逻辑步骤是这样的:《越绝书·记地传》说:“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明万历十五年编修的的《绍兴府志》说:“越王允常冢在木客山”,“木客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印山的地理位置与《绍兴府志》所说的木客山地望基本相符。根据上述两条文献资料,《简报》说:“所以我们认为,印山大墓即为史书记载中的‘木客大冢’,大墓主人是越王允常。”我们认为,仅凭如此单薄的证据,下如此重大的结论,有轻率之嫌。因为:
第一,正如《简报》所说,印山“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小山包”,有些绍兴学者认为它不属木客山。
第二,即使印山属古木客山的一部分,印山大墓也不一定就是允常的木客大冢,二者在逻辑上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根据笔者对《绝对书》有关记载的研究,勾践葬在琅琊,夫谭、允常的墓,可能也已迁到琅琊,允常墓未必还在木客山。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2]为节约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根据对印山大墓的体量规格、工程水平分析,它与允常时期的越国国力太不相称,它肯定不是允常墓。春秋时期,不但越国造不出这样的墓,吴国也无法企及。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印山越国王陵》,《浙江学刊》1998年第4期。
[2] 董楚平《越国王室迁葬考》,《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春秋时期,吴越二国的发展水平差距颇大。《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据《者减钟》铭辞,皮已称王,皮即《史记》之勾卑,《索隐》之毕轸,早寿梦二世。[1]越国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舆地志》)。允常与阖闾基本同时,约于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510年之间即位。寿梦元年是公元前585年,比允常即位早70多年,勾卑称王比允常称王当早100多年。
允常虽称王,但国力与同时期的阖闾吴国相差甚大。越国是依违于吴楚之间的附庸小国,而吴国是向楚国霸权发起挑战的“天下”强国。公元前506年,阖闾率吴军直捣楚都郢城,威震“天下”,使春秋争霸的形势发生历史性转折,“天下”霸权从楚国转向吴国。公元前505年,越王允常乘吴军主力在郢之机,从后方偷袭一下吴国。这次偷袭并没有了不起的战绩,也没有重大影响,《左传》仅以“越入吴,吴在楚也”了之。此后,吴国主要精力仍对付秦、楚、齐、晋、宋、鲁、陈诸国,越国虽为近身之敌,阖闾并没有把它看作心腹大患。直到11年以后,即公元前496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槜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次战争,越国赢得有些侥幸,且不彻底,没有乘胜追击,攻入近在咫尺的吴都。相反,三年后,夫差报复,直捣会稽,几亡越国。
《吴越春秋》多小说家言,措词甚不严谨。如说“越之兴霸自元(允)常矣”。近代有些历史学家据而说允常已称霸,近来有些学者据此而说印山大墓的规模气势与允常“兴霸”相一致。霸是伯的借字,伯者,长也,诸侯之长才能称得上霸主。现有历史资料,并不能提供允常称霸的事实,越国是从勾践灭吴以后才开始称霸的。“越之兴霸自元(允)常”,充其量只能理解为越国后来之所以能称霸,追溯根源,肇始于允常的“拓土”、“称王”。
[1] 马承源《关于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第1期。
春秋中晚期,吴越地区已进入成熟的青铜时代,青铜文化水平是国家实力的重
要标志。现存吴国春秋中晚期的具铭铜器,有勾卑时期的“者减钟”10件,寿梦时期的“邗王是野戈”1件,诸樊的“工䲣太子姑发剑”与“工䲣王剑”各1件,季札的“工䲣季生匜”1件,“工䲣大叔盘”1件,余祭的“攻敔工叙戟”1件,“余昧予”1件,王僚的“伯刺戈”1件,“吴王光鉴”2件,“吴王光残钟”约13件,“攻敔王光剑”4件,“攻敔王光戈”2件,“吴王光戈”3件,太子终累的“配儿钩鑃”2件,“玄之用戈”1件,“吴季子之子逞之剑”1件,夫差为王子时所作的“王子于戈”2件,“吴王夫差鉴”5件,夫差的“禺邗王壶”2件,“敔王夫差盉”1件,“攻敔王夫差戈”1件,“吴王夫差矛”1件,“攻敔王夫差剑”10件,“攻敔臧孙编钟”9件,“吴王御士簠”1件,“无土脰鼎”1件。共计81件,器类14种,其中4件错金。[1]春秋时期越国的具铭铜器,人名可考者只有2件作于允常时期、工艺简陋的《越王之子勾践剑》[2]。工艺超绝的《越王勾践剑》应该“是在灭吴之后”所作,当时越国“继承了吴国的先进技术,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后来居上,一跃而达到高峰。”[3]越灭吴是公元前473年,历史已进入战国时期。
春秋晚期,吴越二国青铜文化水平的天壤之别,是其社会发展水平的反映。但是,春秋晚期吴国王陵的规模远不如印山大墓,也有天壤之别。
从江苏省丹徒县谏壁至大港的沿江低山丘陵上,分布着一系列吴国大型墓葬,是吴国的王陵区。[4]王陵的年代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著名的西周宜侯矢墓即在这座山上。春秋时期的王陵有北山顶大墓[5]、青龙山磨子顶大墓等。北山顶大墓是吴王余昧墓。磨子顶大墓是这个王陵区的第一大墓。在1994年发现苏州真山大墓、1996年发现绍兴印山大墓以前,它还是“江南地区”“春秋第一大墓”[6],应该是春秋晚期某位吴王的陵寝。1994年发掘的苏州真山大墓(DPM1)是目前发掘的最大的吴国王陵。吴国的政治中心原在宁镇地区,阖闾始都姑苏,夫差是亡国之君,真山大墓的主人应该是阖闾。
封土台底部东西长70米、南北宽32米,墓底至封土顶高8.3米,诚如报告所
[1]以上资料,详见拙撰《中华文化通志·吴越文化志》第四章《吴国金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近年发现的新资料未统计在内。
[2]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3]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4][6]肖梦龙《吴国王陵区初探》,《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5]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言,是苏南地区包括镇江发现的东周封土大墓中规模最大者。使用多层棺椁,随葬的精美玉器是苏南地区包括镇江发现的东周大墓所不能比拟的。其规格之高,与中原地区同时代封国国君的墓葬相比亦毫不逊色。发掘报告作者推测其为吴国某代国王的王陵不是没有根据的。[1]
这座苏南最大的吴国王陵,与中原地区同时代封国国君的墓葬相比虽然“毫不逊色”,但与僻处钱塘江以南的印山大墓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看了印山大墓,回头再看看丹徒吴国王陵区,更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今将印山大墓与苏南三座吴国王陵列表比较于下。
墓葬填筑膏泥,以楚墓最为普遍,填炭见于中原墓,既填膏泥又填炭,并在墓山周围挖掘隍壕,则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代秦公陵园。一般来说,楚文化、中原文化是要先经宁镇地区、太湖地区,然后传到钱塘江南岸的。春秋时期,吴国受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影响明显大于越国,而丹徒的吴国王陵区与苏州的真山大墓,皆未发现膏泥、木炭与隍壕。远在钱塘江南岸的印山大墓,却非常完整地接受了这些外来文化,其时代非在灭吴称霸以后不可。
综上所述,印山大墓绝不可能是允常之墓,它只能是战国时期某位越王的陵寝。那么,印山大墓的主人是战国时期哪位越王呢?
[1] 李伯谦《真山东周墓地·序》,文物出版社,1999年。
《越绝书·记地传》说:“独山大冢者,勾践自治以为冢。徙琅琊,冢不成。去县九里。”勾践大冢是个未完成的工程,后来因迁都琅琊,勾践也就葬在琅琊。印山大墓应该是勾践子孙之墓。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引《纪年》说:“翳三十三年迁于吴,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乱)。”越王翳三十六年是公元前376年,从这年开始,越国内乱,国力开始衰竭。印山大墓不可能作于这年以后。
勾践的儿子是鼫与,从鼫与至翳,共有四王,他们在位年代如下:
鼫与(金文作者旨于赐),公元前464年至公元前459年,在位6年;
不寿(金文作丌北古),公元前458年至公元前449年,在位9年;
翁(金文作州勾),公元前448年至公元前412年,在位37年;
四王中,者旨于赐在位时间最短,仅6年,但他在位期间的传世铜器器类最多,质量最高,数量最大,计有“越王者旨于赐钟”1件,错金;“越王者旨于赐剑”9件,其中1件错金;“越王旨者于赐矛”4件,其中2件错金;“越王者旨于赐戈”3件,其中2件错金;“铭文双钩的越王剑”1件;“於字残钟片”1件;“越大子不寿矛”1件。[1]共20件,其中有6件错金。吴国从勾卑到夫差100多年间81件青铜器,只有4件错金。越国传世具铭青铜器共72件[2],者旨于赐在位6年就有20件。越国传世具铭铜器器类简单,只有剑、矛、戈、钟、勾、鑃、鼎六种[3],者旨于赐拥有前四种,是越国诸王中铜器器类最多者。越国具铭铜器有9件错金[4],者旨于赐有6件,占2/3。1995年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越王者旨于赐剑”,工艺超绝,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并列为越剑之双绝,国家之重宝。者旨于赐在位仅6年,其铜器的总体数量与质量竟能胜过所有在位时间比他长的其它越王,这说明者旨于赐时期,是越国国力的鼎盛期。因此,者旨于赐是有能力营造印山大墓的。此外,不寿、州勾、翳,都有可能是印山大墓的主人。相比之下,者旨于赐的可能性最大。
有人说《越绝书·记地传》没有写到勾践子孙的墓葬,可见他们不葬在绍兴,而是葬在琅琊。这是不成逻辑的推论。《越绝书·记地传》主要写勾践遗迹,对勾践子孙,不但没有写他们的墓葬,而且没有写他们其它方面的事迹与遗迹。《越绝书》没有写到上述四王的墓葬,不能成为排除上述四王是印山大墓主人可能性的理由。
[1][2][3][4]董楚平《中华文化通志·吴越文化志》(上编)第五章《越国金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总之,印山大墓缺乏判断墓主人的直接证据。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其年代应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根据墓葬的规模、规格与建筑技术判断,它肯定是越灭吴后某位越王的陵寝。勾践的势位与印山大墓最为匹配。但根据《越绝书》记载,勾践迁葬琅琊,我们只能在勾践子孙中考虑墓主。根据勾践子孙的传世青铜器判断,墓主以勾践之子者旨于赐的可能性较大。假设《越绝书》关于勾践迁葬琅琊的记载不实,那当然要另作别论。不过假设要有一定的根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推翻《越绝书》的相关记载。
附记:勾践之勾,勾吴之勾,或作句。我在1999年以前所写的书示中,也勾、句混用,未统一。1999年,我在《中国语文》第6期发表《浅谈“勾践”与“句践”的纠纷问题》一文,“建议把读gōu的‘勾吴’、‘勾践’、‘勾章’、‘勾鑃’之句,都统一为勾,不作句。”(第449)从所以后,我一直身体力行,观点弥坚。但个别拙示发表时,勾字却被改为句,这是出版过程中出现的意外被动事故,不是笔者观点改变,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