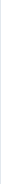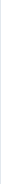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至40年代,他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但是,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他不仅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翻译等方面筚路蓝缕,有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也有独特的建树。他率先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并以民间的眼光来打量民间文化,研究民间文化,从民间自在的文化形态里吸取新的营养,来从事整合新文化传统的工作;他还积极翻译介绍当时西方先进的民俗学理论和古希腊、日本等国的民间文学作品,把民间文化的研究纳入世界的学术视野,为后人开拓出一条研究的道路,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具体地说,是1918年2 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谣。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创办《歌谣》周刊,出版了97期,后并入《国学门周刊》(后再改为月刊)。1923年5 月24日,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它的兴起,与近代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等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外国学术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撞击的结果。作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民俗在“五四”时期受到了新文化先驱者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当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初期,基本上只是限于歌谣或其他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并逐渐扩大到风俗和民间艺术的收集研究。同时,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也开始于“五四”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和周作人无疑对我国的民俗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两人并不是专门的研究民俗的学者,但是他们都十分关注民风民俗及其研究状况,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从事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
鲁迅关注民俗,是站在社会改革的立场上,大力呼吁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破除陋习恶俗。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进化”途中总需新陈代谢,总要破除落后、愚昧、保守的东西。他深感中国的“老例”太多,偶像太多,迷信太多,做事择吉日,出门讲禁忌。因此他曾很深刻地说过:“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1]这段话很深刻地说明了民俗研究与社会改革之重要关系,也表明了他的民俗观,他是不赞成纯学术的民俗研究。他曾举出英国人乔治·葛莱作《多岛海神话》的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2]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到民俗的如《我之节烈观》、《过年》、《送灶日漫笔》、《习惯与改革》等,其目的都不全在民俗研究本身,而在于社会改革,是以民俗事象为突破口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向旧思想、旧道德发难的。总之,五四时期鲁迅的民俗研究,都统一于新文化运动之中,统一于对“世态世相”的揭示和对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他把民俗研究当作了抨击社会现实的工具,这尤其在他的心理和文艺研究上表现突出。同时,“五四”时期,鲁迅运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严肃而又真实地剖析了中国人的性心理结构。比如他从中国旧戏曲中男性扮演女角色的现象中,挖掘出这是国人性心理在长期的封建伦理压抑之下的一种特殊的满足方式:创造了男人扮女人的畸型艺术形式,使“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以此满足了男人和女人欣赏异性的心理欲望。[3]他就这样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在封建伦理道德之下,人们压抑的性心理。鲁迅发表于1928年4月30日《语丝》第4卷第18期上的《太平歌诀》,可以看成是他剖析批判民众愚昧落后思想的代表作。当时在南京建造的中山陵将竣工,在南京市民中流传着一首歌诀,内容是说中山陵合拢之时要索拿儿童的灵魂。这当然纯属人们心理上的禁忌民俗所造成的迷信思想在作祟。但是鲁迅着重指出的是歌谣中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揭示了民众心理的麻木与无知。革命者不去宣传、鼓动、教育民众,民众也不理解革命者的行动,因而才会出现这样荒诞无稽的民谣。
民俗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最直接、形象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而同时民俗是以一定的具象方式体现出来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某个历史阶段上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的载体。民俗发展在时间上所体现出来的代表重大历史特征的这种现象被客观地写入作品,读者就会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通过对具有生活真实性的民俗现象的分析思考,窥视到作品的真正内涵。鲁迅的相当一部分民俗小说就是这样引发了读者的感慨或悲愤,使读者由衷地感叹其作品所达到的历史真实的高度。
鲁迅小说《药》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它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上写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治病这一民俗色彩很浓的故事。它不仅写出了群众的不觉悟,而且通过这血淋淋的民间陋习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群众的悲哀:“先驱者的鲜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在这种深沉的痛苦之中,读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注到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之上,引发起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也是她“崇仰”、“迷恋”民间陋习的结果。通过“在醮”、“祝福”、“捐门槛”等陋俗,我们看到,同样属于劳动人民阶层的婆婆、柳妈,以及周围那些嘲笑祥林嫂痛苦的人,她们所受的传统陋俗的毒害更深,正是她们在精神上再给了祥林嫂以致命的打击,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普通而不幸的悲剧。这一切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陋习在人们心灵深处所留下的厚重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对人物气质、性格等心理特点的形成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有时对人具有一种摧毁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导致祥林嫂们最后走进了地狱。
与以上两例有共同之处的还有《在酒楼上》、《孤独者》、《长明灯》、《伤逝》、《离婚)等小说。这些小说都在乡情、乡俗的后面潜藏了开阔的内在视角,作家一眼注视着世界风云,一眼注视着民族振兴,在这双重视野的汇合交叉点上,构成了作家的“现代意识”。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强烈的时代感,从历史真实的高度暴露了当时的社会,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鲁迅先生的小说存在着一种内在膨胀力,能够使个人的性格膨胀为时代的性格,个人的命运膨胀为民族的命运。”的确,祥林嫂、魏连殳不是一个人,而是旧中国不同阶层人们的不幸遭遇的缩影。
在看鲁迅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很多小说反映了故乡农民的生活,以至这些作品成为20世纪20年代甚至整个中国乡土文学中的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这些取材于故乡生活的小说,无一不体现了鲁迅与故乡农民的精神联系。就他的小说中的悲剧性农民形象来说,鲁迅对他们身上的精神残疾的表现,总是严格地限制在不失农民基本品格的前提之下。诸如阿Q 的勤劳,闰土的质朴,祥林嫂的坚毅,单四嫂子的慈爱,故乡农民的美德,正是这些人物形象的魅力形成原因之一。[4]他要求笔下形象再现故乡农民固有特征的惊人的准确性,其中不无他对农民固有特征的某些偏爱。在他的取材于故乡生活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始终在挖掘农民身上潜藏着的为改变自身不公平的命运而倾向于革命的愿望,他认为:“中国如发生革命,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5]总之,鲁迅“像一个成年的儿子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的农民,默默的而又赤诚的爱着中国的农民”。[6]“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人感到他对农民群众,具有像鲁迅那样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的感情”。[7]由于鲁迅与民间接触较多,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回忆性文字中我们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鬼神信仰等等。可以说,我们阅读鲁迅的一篇篇小说,犹如在欣赏一幅幅故乡的风俗画。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现代民俗学史上,也无疑留下了自己光辉的足迹。在“五四”时期,他与其兄长鲁迅在文坛上是并驾齐驱的战友,两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一个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一个是“战绩斐然的新文化运动的骁将”。[8]正如郁达夫在评说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散文时,非常肯定地说:“中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但是在民俗研究领域方面,周作人比鲁迅较早涉足,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所作出贡献和成绩也比鲁迅大。他于1912年至1914年间所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特别是《古童话释义》,即是运用神话学人类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神话、传说与童话的最初尝试,也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他在写于1913年的《童话略论》里第一次提出了“民俗学”的概念,虽然此概念没有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严格区别开来。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明确阐释了鲁迅的民俗观:鲁迅以批判审美的态度和着眼点出发,以描写民俗事项为手段,通过暴露、扬弃民俗事项的愚昧性、落后性,来惊醒国民,使之能够透过民俗事项的表层,穿透其历史根源和文化内涵,来治愈国民身上的“创伤”,唤醒黑暗的铁屋中沉睡、麻木、愚昧的国民,使之保持“健康的体魄”。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旧中国社会的“病因”,在小说中对封建陋俗作毫不留情的解剖,使麻木的国民“自惭而急于求医”,并使其在“创伤”的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走上苏生的道路。正如杨义在《五四思潮与中国文化》中所说:“他(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不仅表现为掊正统而倡异端,而且表现为离官方而趋民间。” 而与鲁迅出自同一家庭的周作人又是怎样的一种民俗观呢?作为一名现代作家,其研究民俗范围之广,贡献之大,倾注精力之多,少有人比。那么显然存在这个问题:周作人在民俗学这一园地所花精力与功夫为何如此之大?是仅仅因为兴趣?还是出于建设民俗学这门新学科的考虑?还是有其它更深层次的思考?笔者以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周作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俗学家。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杂家”,其民俗学研究固然含有其兴趣的一面,也不可否认显示其对这门学科的建设姿态。在他民俗学研究的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为中国人寻求理想的生活方式。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对于周作人来说,民俗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客观存在的民俗的描述、解释、鉴赏,更是一种主观参与,一种内在的追求:要从‘普通人民怎样活着’的客观考察中,探索一种最适合自己主观性发展的理想的合理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重心所在,他的真正兴趣所在。” 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把民俗研究的“兴趣放到底的广的方面来”,“多注意田街巷坊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
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并非像鲁迅那样固定,一成不变的。1914年,他对绍兴民歌童谣的研究是从个人学术兴趣、风俗鉴赏出发的,目的在于“言语,名尚和风俗鉴赏上”。“五四”时期,在新文化的大潮下,他的民俗研究目的有所变化,转向了社会改革和抨击“世态世相”上来。如《求雨》、《再求雨》就是借民俗事象抨击社会现实的。但是,“五四”运动落潮之后,他的民俗研究又回到了个人的学术兴趣上来。多以“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吃酒”、“喝茶”以及童年时期故乡的节日、饮食习俗为内容,并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习俗中悟出了“自然地简易地生活”的“自然之美”,品出了一般“清淡的滋味”。于是,周作人在研究中发现并肯定了普通平民“自然地简易地生活”、“素朴之中自有真味”的原始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他对于这种“自然”、“清淡”、“素朴”的平民化的生活方式是十分神往的,他自己就一直追求着这种平民化的生活。周作人在《秉烛后谈·序》中写道:“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著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 周作人经常把写作说成“消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文学创作以及民俗研究不应有功利性的观点。在他的许许多多散文创作中,周作人着力表现的也是一种“平常而实在,看来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处”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取自身边生活,如布帛寂粟一样朴实无奇(有的甚至让人觉得琐碎),单看一些作品的题目,即可窥其一斑:如《北京的茶食》、《南北的点心》、《故乡的野菜》、《西山小品》、《乌篷船》、《菜梗》、《苦雨》、《喝茶》、《谈酒》、《卖糖》、《鸟声》、《金鱼》、《苍蝇》等等,所写的都是身边事、常见物、普通人,然而作者正是通过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琐屑小事的叙写,来抒发自己独特的情趣和感受,从而表现出对宁静淡泊境界的向往,这也是他民俗观的中心所在。
《雨天的书》是周作人第一本散文集,其中收入了不少描写民俗的作品。其中《故乡的野菜》是周作人的散文名篇,作者不避凡俗,用温婉的笔调回忆了家乡的妇女、小孩挖野菜的情景:“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自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9]他不仅饶有兴趣地介绍了故乡的荠菜、马兰头、黄花麦果、紫云英等野菜,并且围绕着这些野菜介绍了浙东的民俗,再加上穿插于其间的民谚、童谣,逼真地再现了朴实、温馨的乡野生活,让人难以忘怀。《乌篷船》是公认的周作人此类散文的代表作,它介绍了绍兴水乡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乌篷船,属于舟船民俗范畴。作者从它的形状、构造、规格、所用材料到它的实用特点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对显示着古朴稚拙的民间艺术风格的“船头”,更有精彩的描绘:“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10]最能体现周作人的散文风格的作品,差不多都涉及到了各类民俗,甚至还有涉及域外民俗习惯的,如《日本的衣食住行》等。周作人对民俗的兴趣特别浓厚,就是在被囚禁斗室、失去自由之时,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儿时的“四时八节”的乡风民俗,再次提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儿童杂事诗》甲篇24首,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儿时故乡的新年、上元、中元、清明、端午等节日习俗。至于周作人在失足事伪时期的散文创作,也有不少篇什涉及到了民俗。如《谈宴会》、《上坟船》、《炒栗子》、《撒豆》等等。或许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自始自终都渗透着一种古朴宁静的乡野生活,那闲适恬淡的生活情境是他不可失却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他的身心才能得到真正的放松。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他面对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平淡无奇的内容时,才有着如此的深情。同样,在其他的作品中,如《谈酒》中讲的“酒的趣味,只在饮的时候”,《苦雨》中谈的“仰卧在小船内,更显出郭乡住民的风趣”,《卖糖》中对家乡小儿倾心于“夜糖”的回忆,……这些或雅或俗的情趣,都来自对平和淡泊生活的体验,寄寓着作者的艺术追求,浅淡中蕴深意,读来别有一种韵味。
周作人一生著述广泛,涉及到诸多领域,但对于民俗学、文化形态的研究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善于从学术的、民俗学的角度,去研究民间文学与文化,尤其是神话研究。他曾说:“我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我也喜欢看小说,但有时又不喜欢看了,想找一本讲昆虫或是讲野蛮人的书来看。但有一样东西,我总喜欢,没有厌弃过,而且似乎足以统一我的凌乱的趣味,那就是神话。”[11]在周作人看来,神话不仅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制度、风俗和信仰习惯,而且在文学上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它真诚地表现出了人的质朴的感想。他不仅研究了神话研究的学派、神话的起源及其特点,而且认为神话、传说、民歌等是民族文学的根基,因此,从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内容中发现与个人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周作人民俗学与文化研究中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内容,因为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过程,都不可以与民族的、本土的、民间的精神割断联系。他在《神话的趣味》一文中,讲了天狗吃月的这类传说,当天狗吃月时,家家击锣打鼓,以为可把天狗惊跑了,月亮就能复圆。从前的人很相信月真的被天狗吃吞了,所以便造出许多的神话来,流传至今犹为乡俗。又讲中国小说如《聊斋》里面记载鬼狐的故事很多,并且相信人也可以变成狐狸精。在这里,周作人就说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文学现象,传说变为乡俗,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又体现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独有风格和特点。在《抱犊固的传说》中,他还讲了绍兴城内"躲婆弃"的来历和贺家池的传说,接着认为:“这些故事,我们如说它无稽,一脚踢开,那也算了;如若虚心一点仔细检察,便见这些并不是那样没意思的东西,我们将看见《世说新语》和《齐谐记》的根芽差不多都在这里边,所不同者,只是《世说新语》等千年以来写在纸上,这些还是在口耳相传罢了。”[12]周作人对民俗学与文学创作的这种关系虽没有明确的文艺或道德上的价值判断,但却指出了民俗学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深层联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张扬“人的解放”的运动,作为人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周作人,他长期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对中国本土的民间文化充满着浓厚的兴趣。正是有这兴趣,才使周作人的一生中又多了一个闪光点。这一时期,周作人在神话、民间传说、故事、童话、民间歌谣、笑话、谜语、宗教、迷信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对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研究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应该说他的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我国早期民俗学的建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下文笔者以周作人在民间歌谣方面的收集与研究为例,来说明他对我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周作人曾在《周作人自述》中写道:“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13]作为一个大学者来说,这样的自述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已,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注意到了歌谣,他自己也承认是因为对日本的戏曲感兴趣进而注意到歌谣的,同时他本人也颇喜欢英国的民间歌谣,在他的《海外民歌译序》中曾写到:“我平常颇喜欢读民歌,这是代表民族的心情的,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与个性的诗之难以捉摸者不同。在我们没有什么文艺修养的人;常觉得较易理会。我所喜欢的是英国的歌词。(Ballad),一种叙事的民歌,与日本的俗谣,普通称为‘小呗’。”[14]在《知堂回忆录》中,他曾提到日本作家佐佐醒雪和高野斑山对他的以后收集研究中国民间歌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佐佐醒雪的那套与民谣相连接的抒情歌曲集《俗曲评释》,可谓是他接触正式歌谣的开端,虽然以前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时也接触过一些类似于歌谣性质的民间故事,但这一回的影响却非同寻常,这一次使他在民间歌谣方面的研究开了“历史的先河”。另外,周作人还深受佐佐醒雪《近世国文学史》的影响,“其中有两章略述歌妓与净琉璃二者发达之迹,很是简单明了,至今未尽忘记”。而高野则是专门从事日本民间歌谣的专家,他编过《俚谣集拾遗》,著有《日本歌谣史》,还编辑“日本歌谣集成共十二册”。[15]周作人晚年回忆起这些如数家珍,可见他当初对这些书和作者是专门留意并且研究过的。同时,周作人还深受日本乡土研究专家柳田国男之影响。1910年,在周作人离开日本的前一年,他买了一本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这是刚出版的新书,共总刊350部,周作人所有的是291号。因为书面略有墨痕,想要另换一本,书店的人说这是编号的,只能顺序出售。这一件小事周作人一直没有忘记,直到晚年还津津乐道,而最难忘的自然是这本书给周作人指示了民俗学的丰富趣味,尤其是柳田国男强调的“乡土研究”,使周作人懂得了要真正了解一国的文化,必须深入到普通人民生活街头巷尾里去。[16]
那周作人是何时动手收集民间歌谣的呢?早在1913年,周作人兄长鲁迅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他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特别是他在绍兴县教育会当会长期间,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他在《绍兴教育会刊》一月号上刊出一个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风土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济之嬉游,母姊之话语,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繁重,非一人财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17]遗憾的是,广告登了几个月,只有一个人送去了一篇儿歌,而周作人自己却收集了不少的歌谣。他从范啸风的《越谚》中转抄了五十五篇,自己亲自收集了七十三篇,别人帮助收集了八十五集,编成一卷《绍兴儿歌集》。直到蔡元培和北大的介入,此事才发生了转机。1918年春,在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诸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1920年改为歌谣研究会,并把征集到的近世歌谣在校刊上连载,直至1922年。其实早在“左翼文学”形成之前的20年代初,由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顾颉刚等“五四”知识分子发起的“歌谣研究”,便已开始对民间话语资源的收集,后来被纳入到了民俗学的研究中去。1922年12月17日举行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并创刊《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等负责编辑,周作人先生且亲自起草了《歌谣》的发刊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旧文化的思想改革运动,五四时期也是“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发达”,人类意识觉醒的时代,人们正是以这样觉醒的观点去看待民俗的意义。刘半农在顾颉刚编《吴歌甲集》序言里说:“这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干脆说来,就是民族灵魂”;又说:“吃饭穿衣等事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所以要研究各民族特有的文明,要彻底了解各民族的实际,非求之于吃饭,穿衣等方面不可,而民歌俗曲,却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18]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民俗学是以国民性的研究为其主要目的与内容的——它是以国民的生活整体(习俗、日常生活、信仰,以及民间文艺)为对象,进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或者说是从民族生活史入手,研究与把握民族精神文化。[19]
周作人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包括国民性)有一个独特的观察,他认为,“国民文化程度不是平摊的,却是堆垛的,像是一座三角塔”。[20]民族精神文化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先觉者已经达到的水平,要在全民族全社会中普及,成为普遍的平均水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周作人由此而得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结论:“研究中国文化,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所见应比较地更近于真相。”[21]因此,他一再地告诫民俗研究工作者,要把研究“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街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22]因此,在五四时期,对于周作人本人最有意义与最有影响的事,自然是关于歌谣的搜集与研究,宾试图利用歌谣的影响来“改造国民性”。他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23]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以后,根据周作人的建议,歌谣研究会又改名为“民俗学会”,扩大歌谣收集范围,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在其列。正是在民俗学会的指导与推动下,更全面地展开了我国民俗学研究,并且很快出现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等一批最初成果;周作人为之作序的就有刘半农《江阴船歌》、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林培庐《潮州畲歌集》、江绍原《发须爪》、谷万川《大黑狼的故事》等。[24]
我们知道,有很多民间歌谣中不免带有一些猥亵成分,因此它在学术活动中倍受冷落,因此在1918年,北大开始征集歌谣的时候,最初便简单地规定了入选歌谣的资格,是“征夫野老游妇怨归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可以入选。后来根据周作人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1922年发行《歌谣》周刊时才改了章程。其中第四条寄稿人注意事项说:“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这才为猥亵的歌谣争得了一点“生存权”。1925年10月,周作人与钱玄同、常惠联合署名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计划编辑《猥亵歌谣集》及《猥亵语汇》(后未果),以“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也就是咱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兴味”。同时他本人认为,歌谣当中谈及爱情的部分,因为著作者的态度是自然的,顺乎人性的,因而也是道德的。他在《人的文学》中说:“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注意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于著作者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同时,周作人还分析了造成民间歌谣有猥亵成份的原因,一是“民间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二是“中国的特别文字”犹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大原因。因为中国文字复杂,民间诗人运用不了,就用通俗甚至粗俗的口语表达感情;第三,则是中国人生活的不完满,他说:“中国社会中的禁欲思想虽然不很占势力,似乎未必有反动,但是一般男女关系很不圆满,那是自明的事实。我们以为两性的烦闷在时地上都是普遍的,民间也不能独居例外,……猥亵的歌谣赞美诗情种种的民歌,即是有此动机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别求满足的方法。”[25]他从民间的道德观念、两性生活的状况、文字使用的难度等方面分析了猥亵歌谣产生的原因,使人们对民间歌谣中猥亵成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
那周作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民间歌谣的收集与研究呢?他认为,收集和研究民间歌谣有益于对民俗学的研究,他甚至认为民俗学对歌谣故事的研究比仅仅从文学史角度的研究来得更为重要,在《歌谣》中说:“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言语学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参考的材料。”[26]在这里,他提出了二点,一是考见国民的思想,可以研究风俗与迷信,二是对语言学的研究有帮助。
周作人对民俗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散文和对中国民间歌谣的收集与研究上,同时他对民俗儿童文学方面也有所偏爱,周氏对民间童话的界定在周作人的民间文学分类中,几乎涉及了我们今天所划分的所有体裁,即有神话、传说、童话、动物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寓言、歌谣、戏曲等,这在本文中不加以论述。通过以上对周作人民俗学方面的梳理,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周作人对民俗学研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从学术的角度去探索民俗文化,他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民俗文学研究中起到了拓荒的作用。总之,周作人对民俗学的研究,有其独特的出发点和新颖的研究态度,这些见解放在我们现在的民间文化研究中也并不过时,应该引起我们当代民俗学研究者的重视。
[3]、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黄开发:《人在旅途 : 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卜立德(英国):《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 :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裘士雄:《鲁海拾贝》,大连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3]、杜一白:《鲁迅的写作艺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14]、张杰、杨燕丽:《鲁迅其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5]、林非:《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16]、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7]、姜彬:《中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1991年7月版。
[18]、童庆炳:《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
[19]、顾琅川:《知堂情理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6月版。
[20]、《文艺论丛》第8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4月版。
[21]、张铁荣:《周作人评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22]、廖海波:《鲁迅创作中的民俗视角》,《民俗研究》,2002年第一期。
[23]、袁靖华:《论鲁迅小说中的民俗表现》,《邯郸师专学报》,2002年3月版。
[1]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二》,《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叶振忠:《鲁迅周作人民俗观之比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4期,2001年7月版。
[4]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第126页,百家出版社,1996年3月版。
[5]鲁迅:《华盖集续编·〈阿 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第127页,百家出版社,1996年3月版。
[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第7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8]李子和:《信仰·生命·艺术的交响——中国傩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周作人:《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第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0]周作人:《泽泻集·乌篷船》第2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1]刘春香:《周作人散文的冲谈美》,《阴山学刊》第17卷第3期,2004年5月版。
[1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抱犊固的传说》第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3]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上册)第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周作人:《谈龙集·海外民歌译序》第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5]罗兴萍:《浅论周作人民间歌谣研究》,《无锡教育学院学报》第20卷第4期,2000年12月版。
[16]钱理群:《周作人传》第15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
[17]周作人:《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载1914年1月20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
[19]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69页,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
[20]周作人:《谈虎集·拜脚商兑》第1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21]周作人:《看云集·拥护达生编等》第13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22]周作人:《立春以前·风土志》第1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23]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9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24]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67页,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
[25]引自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纪念增刊,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5年印影版。
[2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第36—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