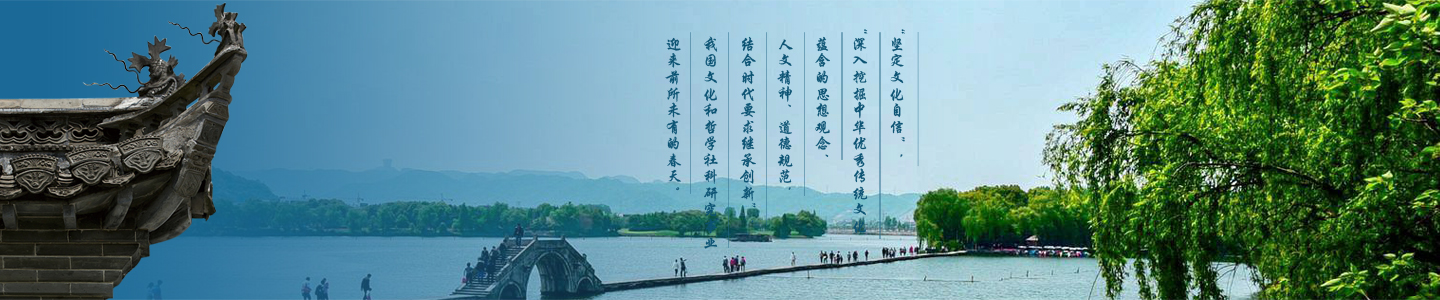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中期,绍兴市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过程中,把“建设以历史文化和山水风光为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自己跨世纪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对于其中的两个特色,人们对前者大都比较熟悉,而对后者则比较陌生。而实际上,这两个特色的提出都有着充足的依据。就前者而言,绍兴是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自不待言;而就后者而言,唐代的元稹和白居易就分别有“天下风光数会稽”和“东南山水越为首”的评价。直到明代的刘基还说:“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在历史上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绍兴确曾是一个以山水风光称著的城市,以至有“山水国”、“山水郡”和“山水州”之誉。当然,“山水风光”与“历史文化”其实并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概念,因为说到底,“山水风光”也属于“历史文化”的范畴,而且在二者之间还相隔着“山水文化”这个层次。
山水,是构成人类生态环境的主要基础和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对象。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总是根据自身当时的需求和力量,对山水加以利用和改造,使之符合于自身的目的,从而成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部分与山水相联系的人类文化,我们把它叫做“山水文化”。要而言之,山水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与山水形成各种对象关系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晶。
由于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需求和对客体的感知能力、利用能力、改造能力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与之相适应,山水文化也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同时,由于主体本身的需求和目的不同,指向同一客体的对象化活动也会具有不同的重心和意义。这种情形,无论在历时性上还是共时性上都是普遍存在的。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历史时期水山文化的重心,大致经历了实用的、宗教的、哲学的和审美的这样几个阶段。而在其共时态上,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在依次发生之后,不但长期共存,而且又相互联系,彼此制约,深层互渗,从而复合出绚丽多彩的山水文化现象。
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山水文化是随着人、社会、自然这三者之间的繁复适应和关系演进而协调发展的。它历史地分享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兴衰,凝聚着人们的需求、目的和本质力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因此古人常说,游山如读史。在山水文化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艰难奋进的历史面貌。
同绝大多数人类文化现象的起源一样,人类与山水的关系,也发端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即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的需要。在此阶段上,山水的实用性具有至上的意义。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和“大禹治水”的传说,便从否定的方面反映出人们心目中关于山水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山水文化,可以称之为实用的山水文化。这种山水文化的发展,显然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
在绍兴的山山水水中,保留着人类利用、开发和改造大自然的丰富遗迹,流传着许多赞颂绍兴先贤创造物质文明的口头传说,历代的方志史籍中也作了大量的记载。从特定视角看,绍兴数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山海经”。古绍兴依山傍海,美丽富饶的绍虞平原,是绍兴历代劳动人民及其领导人物通过呕心沥血的经营和胼手胝足的劳动,从山与海的结合部上开创出来的一片土地。这正如陈桥驿先生在他的《绍兴水利史概论》一文中所说:“绍兴,这个良畴沃野、河湖交织的鱼米之乡,它其实是历史时期水利事业的产物。”
这种坚韧不拔的努力早就开始了。流传至今的禹禅会稽、禹娶涂山、禹会会稽、禹诛防风、禹葬会稽以及大禹治水毕功于嵊州了溪等传说,成为绍兴文明史波澜壮阔的序幕。
春秋战国时期,绍兴的山水被更多地打上了“人化”的印记。“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对于越国来说,会稽山不仅是于越部族的发祥之地,而且一直是其军事上的腹地堡垒,经济上的生产基地和政治文化上的宗教圣地。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会稽山中星罗棋布,不可胜数。如一大批山头就因越国的经济活动而得名。其中有采集和种植的蕺山、稷山、葛山、麻林山;有养殖和狩猎的犬山、鸡山、豕山、白鹿山;有开矿的姑中山、赤堇山以及作为冶铸场所的铸浦、上灶、中灶、下灶、日铸岭等等。对山洪和海潮的斗争也在较大的规模上进行。史籍上关于“庆湖”的记载,反映出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山会平原的南部已有了局部的开发和利用。到了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时期,围堤筑塘以开发沼泽平原的水利工程大量发展起来,并逐渐由南向北推进。后世的南塘(湖堤)、北塘(海堤)以及与会稽山北流的众多河流直交的东西向运河(浙东运河)都初露端倪。
秦一统以后,秦始皇为了消解于越部族潜在的力量,巩固国家的统一,亲自到这一地区巡视,从而留下了秦望、望秦、刻石等山名。秦始皇把会稽郡的郡治设到今江苏苏州,又把“大越”改名为“山阴”,降为县级建置,以削弱这里的政治影响。秦始皇还以强制的手段把于越部族的主体迁出这一地区,大量越人抵制迁徙,又向南部流散。这时,虽然有一些中原人口在秦始皇的安排下由外地迁入,但仍无补于这里“地广人稀”局面的改变,地区经济一度衰落。
经过西汉一代的经营和恢复,到东汉永建四年〈129〉实现吴、会分治,山阴县城成为会稽郡治,这说明地区经济又重新获得了发展。吴、会分治后不过11年,我国东南地区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鉴湖就告诞生。鉴湖,这个我国东南地区最早最大的人工湖泊,是东汉太守马臻在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主持修建的。它南依会稽山脉,北至人工堤塘,东抵东小江(今曹娥江),西近西小江(今浦阳江),控制集雨面积610平方公里,水面面积172.7平方公里(约为今杭州西湖的30倍),正常水位在5米高程上下,正常蓄水量2.68亿立方米。总库容量在4.4亿立方米以上。湖中共有115个岛屿,面积17.23平方公里,又以绍兴古城南自稽山门至禹陵的一条长约3公里的驿堤为界,划分成东、西两湖,分属会稽、山阴两县。作为水利工程,古鉴湖的主体是北缘的堤塘,历史上称为“南塘”(与杭州湾南岸的海堤“北塘”相对称)。据考证,古鉴湖堤塘东起嵩口(今上虞嵩坝镇)斗门,经白米堰折西,沿陶堰、皋埠至城东,环城南而过,由偏门折西北,迄于今绍兴县钱清镇大王庙村的广陵斗门,全长56.5公里。
古鉴湖的筑成,标志着绍兴地区开发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跃进,使绍兴逐渐发展成为富甲江南的鱼米之乡。一方面,巨大的水体造成了鉴湖地区极为发达的水产业,“茭、荷、菱、芡之实不可胜用,鱼、鳖、虾、蟹之类不可胜食”;另一方面,充足的淡水资源被迅速用于鉴湖以北沼泽平原的改良,到六朝时,“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值一金”。同时,古鉴湖的筑成,还给绍兴带来了一个始所未料却功效长久的收益,即极大地优化和美化了绍兴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会稽山在与鉴湖的相依相拥中彻底地改变了它的外在风貌,从而为审美的山水文化在这里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文人雅士趋之若鹜的山水旅游和文化旅游的热点地区及宗教兴盛之地。
人类受惠于自然,取之于自然,同时也受制于自然。在文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众多自然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支配自然的能力很低而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人对自然既有亲近的一面,又有敬畏的一面,这种情形必然引发出人对自然的崇拜,这是人类与自然宗教关系的体现,可以称之为宗教的山水文化。初民们或相信山水为神灵所主宰,或以为山水本身就是有意志的神灵。《礼记·祭法》中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抱朴子》中说:“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也。”根据这种认识,人们就选择适当的山川之地定时去进行祭祀,以祈求或酬谢山川的赐予和庇护。
在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对山川的祭祀中增添和突出了政治的内涵并为统治者所掌握。天子遍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则祭其国之山川。祭祀的场所随之更加神圣。在绍兴,“禹禅会稽”是山川之祭可以追溯的起点。由于此举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使会稽山得以在历史早期一直以江山社稷的象征雄踞于中华九大名山之首,位在泰山之上。越王勾践行诸侯礼制,“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继续把会稽山列为国家大祭的对象。秦一统以后,秦始皇不远千里,临会稽,祭大禹,刻石纪功,并以会稽山为名山,祭用牲犊圭璧,敬礼有如。以后历唐宋元明,各朝对会稽山均有赠封:唐封“永兴公”,宋封“永济王”,金封“永兴王”,元封“昭德显应王”,明称“会稽山之神”。到清代,对会稽山依然是“祭祀惟谨”。至于座落在会稽山麓的南镇庙,其香火之盛,则一直延续到更为晚近的时期。
另一方面,从对水泽的祭祀传统中也孕育出“兰亭”这一名胜之地。因为追本溯源,“修禊”之礼乃是从古代水祭祀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民俗事象。
在中国古代,有儒、道、佛三教之说。其实,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教”只不过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充其量只能称作“说教”,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决定了不可能从儒家学说中发展出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宗教的因素)。相反,具有浓厚出世倾向的道家学说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这一点。道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本土宗教,它的形成虽然是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和推动,但却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继承和吸收了中华原始宗教的大部分成果。由于在原始宗教中,山水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崇高的地位,因此道教也就与山水有了密切的关系。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老,肉体成仙,自由快乐。仙人所居的“仙境”,如“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并非存在于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而无一不在现实世界的美妙山水之中。即使是远在“海中”或“海外”的“三岛十洲”,实际上也没有脱离人间的大自然。
在绍兴,会稽山为第十洞天,沃洲山、天姥山、若耶溪、司马悔山分别为第十五、十六、十七、六十福地。上虞的凤鸣山,因道教理论家魏伯阳的传说和古迹享有盛名;嵊州的金庭山,历史上曾有“毛竹洞天”之称。此外,道教的宫观,也多建在这种风景优美的地方。如越中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道观——龙瑞宫,就座落在宛委山南麓的涧谷之中。
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它在传入中国以后,通过大量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而成功地实现了风土化,所以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中国的山水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天下名山僧占多”。在历史时期,我国逐渐形成了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和四川峨嵋山这四大佛教名山。这四座山,相传分别为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场所,故又称为“四大道场”。此外,佛教中还有“八小名山”,分别是北京的香山、陕西的终南山、河南的嵩山、浙江的天台山、云南的鸡足山、湖南的衡山、江西的庐山和江苏的狼山。佛教各宗派的祖庭也多在山青水秀的地方。据《中国佛教史》言,中国佛教走上独立的道路,是以两晋之际掀起的般若学思潮为标志的。对般若学的解释,当时有“七家六宗”之说,其中六宗的代表人物,当时均在今新昌东山、沃洲山、石城山一带修行,在唐代白居易所撰的《沃洲山禅院记》中有“凡十八僧居焉”的记载,说明当时剡中确曾是佛学思想的一个研究中心,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绍兴会稽山核心区,佛教在禹陵附近争取到一座重要的山头——香炉峰。今天山上寺宇毗连,宝塔高耸,香火旺盛,已成为绍兴市区佛事活动最主要的场所。而在历史上,则以云门寺最负盛名,最具规模。《康熙会稽县志》载:“云门山,在县南三十里秦望南。晋义熙二年(406)中书令王献之居此,有五色云见,诏建云门寺。后析为六:曰广孝,曰显圣,曰雍熙,曰普济,曰明觉。”云门寺在历史上曾有过相当繁华的岁月,宋代陆游在《寿圣院记》中说:“云门寺,自晋唐以来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时,缭山并溪,楼塔重复,依岩跨壑,金碧飞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观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虽寺中人,或旬月不得觌也。”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佛、道二教在山水中的活动和建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山水文化的内容。僧道们或穷搜群山,发现自然景观;或建寺造宫,构筑人文景观,客观上成为开拓山水景观的先驱者。那些洞天福地、仙居道场以及名寺名观,不仅记录了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一部物化的宗教史,而且又是历代文物荟萃的场所。历代的建筑家、雕塑家、园艺家、书画家等各色艺人和能工巧匠,都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他们的传世杰作。历代高僧名道、文人隐士以及帝王将相、江湖豪杰的遗迹,也引起后人无限的兴趣和追念。
审美的山水文化,通常叫做“山水风光”。绍兴的山水风光,乃是绍兴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一个有物质载体的精神文化现象。用哲学的语言说,文化,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在真善美诸方面发展水平的范畴。是人类处理其与客观世界的多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和解决自身心灵深处永恒矛盾的方式,是人类的主观心态、实践活动及其产物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人们为了审美的需要,把山水自然作为自己审美实践的对象和审美力量外化的载体,其结果便构成了山水风光的内容。由于人类的审美实践主要地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因此山水风光也就主要地表现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但是,人们也往往利用物质的手段来改变山水的面貌以符合自己的审美尺度,于是山水风光的实现便在精神和物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都获得了直接的通道。
要而言之,审美的山水文化,是人类本质中审美力量对象化的结晶,体现着人类与自然亲近和和谐的关系。在中国审美的山水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智慧,融合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自然观和生命观,并折射出中华民族集体性的心理、意识和时尚。
审美意识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先人们超越实用的观点和宗教的观点,而用审美的观点看待自然,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的山水文化起了奠基的作用。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在他看来,人们在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中可以获得对自己道德意志和人格力量的审美体验。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后来的庄子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他们看来,人们似乎应该更注重于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中去领悟和体验“道”的真谛。
儒家的这个“比德”说和道家的这个“法自然”说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一直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山水审美的主旋律早在它的萌芽时期就已经被儒、道两家的祖师爷一锤敲定。
时至秦汉,帝业发达,四方一统,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大为扩大,人们的视野更为宏阔。秦始皇巡视天下,张骞凿空西域,司马迁壮游四方。尤其是汉末的曹操,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气势,抒发出志向与景观两相交融的情感,这充分表明人类对山水的态度,已经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国山水审美的喷薄时代就要来临了。
山水之美,虽以其本身的自然尺度作为基础,但自然物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又是人们认识、利用、征服和开发自然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不断地改变着其与对象世界的关系,而人类只有在与山水的实际较量中获得了改造山水以适应自身需要的显著成果,并对自己的这种力量建立起充分的自信心,感到自己与山水已经处于平等甚至优越地位的时候,才会对山水提出完满性的要求和期待。产生审美的冲动。
在中国,人们对自然的审美从自发向自觉的飞跃,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这个飞跃的实现,虽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归根到底,它是因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而问世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乱的时代,诸多人生的问题都鲜明地摆到人们的面前,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对峙,社会、自然、精神需求、本能与道德之间发生了种种冲突,儒、佛、道相互攻讦又相互渗透。各家都讲道,但道的指向和内涵却不一样。儒家之道重社会,重人事,具有政治道德的内涵;道家之道重自然,重本性,排斥一切人为的东西;佛家之道重精神,重智慧,主张彻底的清寂静灭。如何整合这些纷纭的思潮,各家不约而同地登上了审美这个层面。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审美活动中沟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在审美层面上为统一“三教”所作的努力。在这种活动中,对山水的审美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山水审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用宗炳在《画山水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意思是说,山水以它的“形”来显示“道”,从而使“仁者”得到审美愉悦。由此可见,魏晋时期人们对山水自然的哲学认识与审美观照几乎是同步的,而仔细审视,其中又有一个逐渐前消后长的过程。举诗歌为例:在兰亭雅集中产生的诗歌,似可命名为“带山水帽子的玄言诗”,而到谢灵运的诗歌,则可称之为“带玄言尾巴的山水诗”了。
一般认为,审美就是对美的事物的欣赏。但中国的传统美学却有所不同,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人认为世上万物都内蕴着“道”的灵性,人与自然都可以被理解为“道”的派生物,“人心”可以在与“自然”的相互观照中体验到“道”的存在,把握住“道”的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审美,主要地不是对物的自然属性的欣赏,而是对物化在审美对象中的自我人格的欣赏。“咏物,隐然只是咏怀”。自然的“物”很少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只有当它成为主观的“我”的载体时,才具有审美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人们在向外走向自然的同时,也向内走向了心灵。又由于心灵深处有一个潜意识的层次,因此当人们愈来愈注重于对心灵深处进行探索时,对心灵的表现和对潜意识的把握就会更加依赖于以山水景观作为观照,后者也因之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的审美价值,并带着浓郁的禅的意味。
隐士在山水审美实践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隐隐朝市”之说的广为流行,隐士成了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道教和佛教的空前兴盛,又进一步壮大了隐逸的声势,形成了天下士、僧、道同隐共游的局面。由于名宦高士共奉隐逸,又从根本了改变了先秦以至两汉隐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满足于隐迹山林,躬耕渔樵,而是寄情山水,热衷于游赏山水以悟道。野隐之士择胜境而栖,朝隐之士造园林而居,山水大自然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六朝时期士人对山水的格外关注,从当时的方志地记中便可略窥一斑。从东汉开始,出现了一些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种地志数量激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时间、内容上看,这些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东汉魏晋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异物”;而晋宋以后,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山水”。从现存绍兴在六朝时期所撰的方志残卷看,情况略有不同。在其前期,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人物,而在后期,关注的对象主要也是山水。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随着士、僧、道生活和心灵的这种山水雅化,游览山水之风大兴。而绍兴,由于各种条件在这里的偶然契合,使它得以率先成为闻名海内的山水游览胜地。在诸条件中,最基本的当然是绍兴山水本身得天独厚的自然尺度。据《世说新语》记载,晋代大画家顾恺之从会稽回去之后,有人问他会稽的山川风光如何?顾恺之以其特有的眼光和语言描述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自此,“千岩万壑”几乎成了会稽山水的一个代名词。对山水,一般可以分作三个层次来进行把握:第一,纯粹自然的山水环境;其二,是自然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山水环境;其三,是反映在人们意识中的理想的山水环境。显然,顾恺之这个审美描述的物质对象是会稽山诸溪水(泛称36源,主要是若耶溪)流域中纯粹自然的山水环境,并不包括鉴湖在内。这种风光,不仅在鉴湖筑成之前早已有之,而且至今仍在绍兴所属县市的山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山水风光”,在其狭义和俗成的涵摄上,指的也就是这种景状。但是,从六朝开始会稽山川之美之所以特别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主要的却在于它已经是一个自然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山水环境。
东汉时期,绍兴的山水环境得到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造,这就是鉴湖的围筑。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浩瀚明洁的鉴湖水在一个纵横百里的宽广空间上把会稽山中的“千岩万壑”组合成为一幅前所未有的山水画卷,其风光正如后来李白所咏:“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由此,绍兴的山水风光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最早由书圣王羲之说了出来:“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他的儿子王献之进一步具体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而唐代的戴叔伦则更加明白地指出:“越中山色镜中看。”“钱塘艳若花,山阴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彼此俱清奇,输它得名早。”明人袁宏道的这首诗,真实地追溯了稽山鉴水在汉唐时期中巨大的旅游吸引力。
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方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和政治中心南移,大批黄河流域的居民纷纷避乱江南,会稽郡成为当时主要的移民聚居地之一,从而大规模地引进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这不仅包括大量的北方劳动力人口,也包括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中原的人才及学术与思想观点。从历史进程看,一方面,这些熟练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绍兴地区经济的发展,使绍兴以“海内剧邑”的实力与建康东西对峙,俨然成为江南的两大都会,以致晋元帝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叹,从而奠定了在隋唐盛世与全国同步起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特别是秀丽的山川风光,正好迎合了当时知识界回归自然,企求心灵超越的思想潮流,使绍兴尤其成为南迁名士的宦游、寄寓和聚会之地。他们对绍兴山水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创作,有力地将绍兴山水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由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所决定,最初能欣赏山水并对山水进行审美创造的,必是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们,具体地说,就是六朝时期的那些玄学名士或隐士。首先,中古山水审美意识勃生的内在逻辑是自然山水的道化和人格化,而这一精神成果直接就是在玄学自然观的诱导下取得的。其次,前面已经说到,六朝时期的隐士与注重内修和自得的秦汉隐士有所不同,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他们提出了“文以艺业”的新观念,致力于以诗文自别于渔父樵夫。在对山水景物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的同时,力图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将自己的情怀和感受凝结在审美的对象之中。这样,别人就能通过他们笔下的理想的山水环境意象来理解和欣赏山水风光的内容。
在历史上,山水诗充当了塑造这种“山水风光”的主力和先锋。谢灵运以其大量描绘会稽山水和永嘉山水的优美之作而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奠基者。自六朝以降,绍兴的山山水水引发出无数佳丽诗篇。这些诗篇从各个侧面发掘出绍兴的山水之美,高水平地塑造了绍兴山水风光的形象,有力地扩大了它的影响和知名度。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到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绍兴的古鉴湖风光也发展到最成熟的时期。“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涨接星津流荡漾,宽浮云岫动虚空”;“漾舟喜湖广,湖广趣非一”;“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试览镜中物,中流到底清”;“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由于这种宽广、舒展、深沉、清凉的风格与盛唐气派颇为契合,因此使唐代诗人们对越州一往情深。
除了古鉴湖风光以外,越州深处的山水风光也没有被人们忘却。相反,由于唐代的知识分子四处遨游成风,剡中山水也获得了人们格外的关注。“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据统计,由于浙东山水名重海内,有唐一代入越来游的诗人不下400余位。他们或从京、洛舟车南下,或自岷、峨沿江东流,间关万里,络绎而至。鉴湖、越台、稽山、耶溪、娥江、沃洲,以及四明,天姥、赤城,天台诸山,处处留下了诗人们的吟鞭游屐,棹声帆影,从而形成了一条被今人命名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古代山水旅游专线和山会、新嵊两大山水风光板块。
唐诗中的“浙东”,系指钱塘江以南、括苍山脉以北、浦阳江以东直至东海这一区域,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唐代诗人游历浙东,主要靠水路。这些水路包括浦阳江、东阳江、永安溪、始丰溪、奉化江、甬江和浙东运河。干线则是浙东运河和剡溪,总长190公里。“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高”。它以萧山西陵为起点,沿浙东运河,经绍兴、上虞,溯曹娥江入剡县,经沃洲、天姥直抵天台石梁。再往后,还可经天台、临海、三门、宁海、奉化、宁波一直到达舟山群岛。不过这后一段游路似乎已到了强驽之末,诗人们的足迹较之在越州境内,显然要稀疏得多了。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诗仙李白曾四入浙江,三到剡中,二上天台,吟出了“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到剡溪”的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闻清猿啼”。诗圣杜甫二十岁时就入越至剡,游冶忘归达四年之久,并自视为少年壮举。“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唐代新乐府运动中坚之一的元稹于长庆三年(823)出任越州刺史,以日日享受湖光山色而沾沾自喜。“时人不信非凡境,试入玄关一夜听”。端坐西湖之滨的白居易到底禁不住好友元稹的诱惑而再度入越探胜,却意外地发现了白氏与沃洲山水之间的悠久渊源,于是欣然命笔撰写了《沃洲山禅院记》。
此外,初唐的宋之问,王勃、骆宾王,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储光曦、王维、常建、綦毋潜,边塞诗人高适、李欣、崔颢,中唐前期的顾况、刘长卿、皇甫曾,“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李端、皇甫冉、李嘉祐,新乐府运动的前驱张继、李绅,苦吟诗人孟郊、贾岛,“诗豪”刘禹锡,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以及唐末的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罗隐等一代名流,都曾盘桓于此。他们的浙东题咏,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份量。
“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唐代诗人为何对新嵊腹地情有独钟。当然首先是因为这里有山水兼胜的自然风光。会稽、四明、天台这三座浙东名山在此间盘结环绕,一条剡溪潇洒流穿其间。两岸千岩竞秀,舟移景换;万壑争流,奔腾有声。直到清代,诗人袁枚游剡溪时,尚有如此咏叹:“看山不厌复,看水不厌曲。剡溪百里中,两景皆到目。”
其次是丰厚的人文积淀。由于山青水秀,环境和平,这里早就成为道教福地、佛教胜地和名士游憩之所。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说:“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兴、渊、支、道、开、咸、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元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丧、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濛、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
此外,剡溪两岸还有大禹治水毕功于了溪的传说,任公子钓巨鳌的寓言,刘、阮遇仙的故事,王徽之乘兴而往,兴尽而返的逸闻,谢灵运伐木开径、木屐登山的壮举。“愿随任公子,欲钓吞鱼舟”;“戴家溪北往,雪后去相寻”;“此中久伫立,入剡寻王许”“庶几踪谢客,开山投剡中”。唐代的诗人们在剡中寻寻觅觅,为的就是追慕魏晋遗风、秦汉文化乃至于史前传说。
但是,从宋代开始,这条诗路上山水风光发展的方向却因古鉴湖的堙废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东汉时期围筑鉴湖的初衷,在于让山会平原的南部蓄淡以加速北部平原的开发。南朝孔令符在《会稽记》中说:“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若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这种功能和效益至少持续了八个世纪。在这八个世纪中,它起到了滞洪和灌溉的作用,使山会平原北部的沼泽地得到了大面积的改造,出现了9000顷旱涝保收的良田。
到唐代,随着海塘工程的全面完成和平原北部河湖网整治的发展,大量淡水北移,鉴湖便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后于公元11世纪前后受到全面围垦,原来的一片浩渺湖水变成了与平原北部一样河湖棋布、阡陌纵横、村舍相望的良田沃野。从此,绍虞平原上成名已久的山水风光就逐渐被今人熟悉和称道的“江南水乡田园风光”所取代。
在今天,完整意义上的鉴湖早已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目前绍兴所呈现的江南水乡田园风光则又远远超出了古鉴湖的范围,几乎可以包括整个绍虞平原。但是,由于这一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在绍兴历史上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至今人们仍然习惯于称绍兴的江南水乡田园风光为“鉴湖风光”。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种清丽雅致一派阴柔之态的“鉴湖风光”与六朝以至隋唐时代雄浑豪阔充满阳刚之气的古鉴湖风光迥然不同,其主要特色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桥、流水、人家”。对于这种风景,陈从周先生在其15首《越州吟》中作了生动细腻的描绘。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古鉴湖虽因大规模垦殖而缩小了六分之五的面积,但毕竟还有约30平方公里的水域留存至今。其中东鉴湖有白塔洋、洋湖泊等,西鉴湖有屃石湖、容山湖等,特别是还有东起越城区亭山乡,西至绍兴县湖塘镇的河段,全长22.5公里,平均宽度108.4米,平均水深2.77米。陆游诗云:“东西相望两湖桥,往来无时一画桡”;“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鉴湖”。这个自南宋时期大致定型直到今天的“鉴湖”,自有一番雅趣别致。在宽阔的湖面上驾舟荡漾,远望青山叠翠,近看碧波映照,湖山碧野之间,飘动的乌蓬船,卧波的石拱桥,傍岸的水际村,以及沿湖的渔箔、渔舍、岸柳、荷菱、鹅侣、鸭群……无不充满着清新朴质、爽目怡情的淡雅之美。“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历代仅有不少文人学士喜欢在这里寓居、漫游,从而又积聚起一批人文古迹,真是一处有一处的故事,一处有一处的情趣。
但是从整体上看,自古鉴湖在宋代堙废之后,绍兴山水风光的知名度便逐渐减少。尤其是新嵊腹地的山水风光,因其游历起点地区同类风光的失落而失去接引,更为人们所淡忘。当然,这条盛极一时的“唐诗之路”的走失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六朝时期,绍兴文化开始实现从一个偏僻落后且一直保持着自身原始内涵的地方民族文化向先进的文化共同体中同构的区域文化的根本性转变。因此,绍兴山水审美文化的演进,不能不受到中国大势的左右。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中国的山水审美开始落潮,人们对山水的审美热情趋于衰退。由于种种历史的复杂因素,这个衰落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要到上世纪末,中国的山水审美文化才在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观念发生整体变化的前提下开始复兴。
在当今的建设生态城市以及旅游开发大潮中,绍兴的山水风光又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浣纱溪、若耶溪、剡溪这越中三大名溪流域内,一个又一个的山水风光景区正在被重新开发出来。昔日漫长的“浙东唐诗之路”,可望再一次出现它所曾经拥有的辉煌。